中國古代文人幾乎都要去當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這樣,他們要么出身貴族,要么是醫生、神甫、律師、商人、教師……的兒子,總之,職業分佈相對寬泛,吃官俸者少。中國古代文人與政治有著深廣而持久的聯繫。
古代多戰亂,不是漢人跟漢人打,就是漢族與游牧少數族打,百年興旺的家族不多。幾位貴族大文人,屈原,嵇康,李煜,李清照,曹雪芹,皆為厄運所造就。
古代文人走向官場或背向官場,其“生存路數”是高度一致的。先秦時代百家爭鳴,像孔子這樣的人連年穿梭於列國,形如喪家之犬而大腦高速運行,想透了很多大問題。秦漢結束了諸子爭鳴的局面,幾百年間雖時有反彈,卻朝著大一統:儒學一統天下。唐宋更以科舉的形式將學問與俸祿直接掛鉤。讀書人,不能金榜題名就得回家種地。 “耕讀傳家”,傳了一千多年。這是中國特色。
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眾多的文人一經入官場,往往把聖人的教導拋到腦後,按官場套路行事,為非作歹者代代有之。像北宋的舒亶、李定,一個狀元,一個才子,幹缺德事卻格外起勁;已經是小人之尤了,他還滿口正人君子。再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詞好,人品卻成問題,他看不起浪跡於底層的柳永,對歐陽修以貌取人,科場做王安石的手腳,安插自家人。
不過,文學大師們好像都是正人君子。
從屈原司馬遷到魯迅,誰不是正人君子呢?
文氣與浩然正氣是連通的。歪風邪氣寫不出傳世文章。阿諛奉承只能寫出令權貴開顏的文章,譬如漢賦。戰國時期,已經有“文學弄臣”這種角色,到漢代,皇權大如天,弄臣們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漢語作派場、列方陣,絞盡腦汁歌功頌德,拍馬屁拍出了高招。
司馬遷抵抗皇權,司馬相如依附皇權,這兩條線由兩位司馬作了開端,長長地延續下來。論數量相如式的人物為多。然而文豪們都排在了屈原司馬遷的身後,為什麼?因為真性情才能留下好文字,虛情假意浮誇拍馬只能得意於一時。誰想去讀那些個扭曲人性的拍馬文字呢?除非他想學拍馬。皇帝和歌頌皇帝的文字一同死去。封建社會歷朝歷代,這類拍馬文字多得數不清呢,卻被歷史輕輕的一巴掌拍進永遠的黑暗深淵。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李白這一聲喊,喊出了無數心聲。
李白的性格在常人看來是有毛病的,杜甫對此感慨說:“世人皆曰殺,吾意獨憐才。”李白的精神有如天馬行空,卻又生活在地上,於是有了矛盾,形成了張力。李白的詩歌藝術受益於這個張力區。猶如冷暖氣流相遇,生風生雨生雷電。
李白為人有毛病,稱不上道德楷模,但李白也是正人君子,一心想做“魯仲尼”似的大儒,安邦定國。他有一顆赤子之心,碰上高力士楊國忠這一類弄權高手,馬上就斜視、就對立了。他在翰林院這種地方狂飲八百天,未必不是效仿劉伶阮藉,雖爛醉如泥而心中雪亮。蘇軾稱讚他:“戲萬乘如僚友,視同儕如草芥。”魏萬頌揚他:“一生傲岸。三十年未嘗低顏色。”
盛唐中唐的翰林學士,多少人學會了進身術鑽營術晉升為宰輔之臣。李白在這個位置上一待三年,卻只管以李白的方式行事,不管皇帝心思,終於被玄宗打發掉了。
唐朝的文人已經很強大了,奔向皇權又越過皇權。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隨身攜帶了兩件寶貝:一是儒家的為政理想,二是鮮明的個性。
在深諳儒學的文人眼中,皇權至尊,但皇帝並不是至高無上的,有兩樣東西製約著皇帝:天意和堯舜時代的政通人和。文人對皇帝念叨天意、堯舜,像念緊箍咒似的,皇帝很頭疼,卻還不敢反駁:反天意反堯舜那還得了,還要不要國運、還坐不坐龍椅啊?杜甫好不容易做了個左拾遺,區區八品官,卻不按唐肅宗的意圖行事,論救房琯,從此失意。失意的杜甫還寫詩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
文人堅持原則,文人不知悔改:“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不能在楚國為美政,於是披頭散發行走在荊楚大地上,走了十年,郢都淪陷之後他縱身跳進了汩羅河。兩千餘年古代史,這是最偉大的自殺,將生命與美政、與祖國的命運緊緊相連。所有的中國人都景仰他,一直景仰到今天,到未來。
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清潔精神,對後世文人影響極大。傑出的文人,腦子裡除了裝著堯舜、孔孟、老莊,還裝著屈子。而自從孟子被奉為“亞聖”之後,他的“民貴君輕”的思想又使文人手中多了一件法寶,一有機會就要亮給君王看。
歷代皇帝,忌憚天意、順應民意、追隨堯舜者,皆為所謂明君。反之則為暴君昏君。
歷代的一流文人,沒有一個是小人;凡為高官者,沒有一個是禍國殃民的。這一層,值得深思。
儒家講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較認真的。
在古代社會的權力格局中,詩人們還扮演著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頌揚聲中頭腦清醒,睜大眼睛辨認著亂象。文人幾乎都是歷史學家,有歷史感,有大局意識。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號再過一萬年也是偉大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一連串耀眼的名字,寫下了傑出的美政篇章。像蘇東坡,更是巴心巴肝為百姓謀幸福,一生輾轉幾萬里,百折不撓,“九死蠻荒吾不恨”,雖堯舜再生也不過如此吧。蘇東坡把中國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極致。他同時又是文化的巔峰期繼往開來的大宗師,文化與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而針對這種結合,尚鬚髮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合?
蘇東坡師從歐陽修,歐陽修眺望白居易,而白居易又緊緊地盯著杜甫……長江後浪追逐著前浪。這就是所謂文化傳承、價值觀傳承、生活意義的傳承。
“品中國文人”的寫作過程中,有些未曾見過的詞彙幾乎自動湧到我的筆下:文化本能,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鏈,文化基因圖譜;生存落差,生活的意蘊層,生活的完整性……我冒昧地寫到文章裡去,似乎得到了讀者的默認。
漫長的古代社會,有著大致穩定的“價值的天空”,覆蓋著巍巍朝堂和窮鄉僻壤。孔廟無處不在。這是華夏文明的特殊性,尚有待喚起深思。解構這塊價值的天空是必要的,摧毀這片天空卻是可怕的,災難性的。人是離開了“意義”就會活得很艱難的一種生物。 “意義”如同蟲子的觸鬚,一旦拔掉就會四處亂轉,“昏天黑地在社會上混。”價值觀的固化和虛無化都會導致災難。西哲如狄爾泰、卡西爾、馬科思.韋伯等早已證明,生活的意義是由文化來維繫的。自然科學追求實證,而文化謀求價值觀,追求生活的意義。文化高於個體生存。
對普通百姓來說,這塊價值的天空可能會顯得有些抽象,但是對蘇軾或歐陽修這樣的文化精英來說,這塊天空是具象的、可觸摸的。文化精英們有良好的文化直覺。
歸根結底,所謂文化,就是讓抽象的東西具象化、讓無形的東西有形化、讓有效的價值普適化。
文化的抽像功能直接源於語言的抽象。
這似乎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語言的大師往往是生活意義的大師。
孔子說:“言而不文,行之不遠。”
這裡的“文”倒不是文飾,不是漂亮詞藻。它是指運用語言的抽像功能洞察生活-社會實踐的能力。
孔子老子莊子,從及後來的釋迦,都是廣義上的文人。
也許可以這麼說:古代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主要是由文人來提供的。
歷代文人都有很強的個性、個體特徵,這也給他們的命運塗上了濃濃的悲劇色彩。由於中國古代文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奔官場、走仕途,所以這種悲劇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作家與此不同。而中西文人在這個層面的對比研究似乎不多見。
古代文人奔官場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這樣的“詩聖”在長安求官求得那麼曲折艱難,給權貴寫詩獻賦的,其內心深處的價值觀卻始終不變。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支撐著杜甫的“不變”?
類似的發問,可以針對很多文人。
文人是堅持個性、堅持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後。古代文人幾乎是失意的代名詞。不堅持就沒有失意。辨析這個綿延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現象,不能倒果為因。
前面提過,孔聖人也是到處碰壁的。
只有老莊這樣的東方大哲,才不跟歷史的進程正面接觸。他們生活在別處,彷彿輕鬆瀟灑地指點著華夏文明的進程。
老莊的智慧迄今是華夏文明進程中的頂級智慧之一。這樣的智慧讓時間的流逝變得無關緊要。誰能測量它的終點呢?有人怎麼也想不通,乾脆把老子說成外星人……
唐宋以來的古代傑出文人,其運思,無不在儒釋道的框架之內進行。這個卓越的、能穿越歷史的文化結構支撐著詩文的不朽,也為今天的哲學性思考提供具有民族特徵的全球視野。
沒有哲思就沒有文學。
尤其在當下,贏得具有民族性的全球視野乃是當務之急。
古代文人的“生存悖論”在於:他在堅持個性與政治理想的同時,也失掉了許多歷史性的契機。比如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三個正人君子、傑出的政壇人物,卻不能抱團形成合力,各唱各的調。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寧願離開汴京到洛陽寫他的。如果他留在中樞,以自己的某些妥協換來王安石的妥協,那麼,熙寧新法的成功面會增大,趙宋的國運或許能好一些。在今天看,王安石的“驟行新法”和司馬光的“盡廢新法”,都含有文人意氣的成分,與現代的政治智慧是有距離的。荊公綽號牛相公,溫公綽號司馬牛,兩條牛狠狠斗在了一塊兒,誰也拉不開。而“一肚子不合時宜”的蘇東坡在朝廷的坦率、坦蕩,“性不忍事”,既令人欽佩,又令人嘆息。
老謀深算的政壇人物,哪能由著性子鋒芒畢露。
而傑出的政治家是既有鋒芒又能內斂,其戰略性眼光和戰術性的步驟高度合拍。
古代文人的意氣用事,北宋政壇可見一斑。意氣用事是說:意氣有用事的空間。而文人的意氣用事對民族心理會產生難以測量的影響。情感、情緒的邏輯暢行時,理性便縮小了地盤。
這當然與“人治”有關。政治理性與製度的構建是同步進行的,古代官員不可能做到這一步。當文人越來越像個文人的時候,他離他想要追求的理想政治就越來越遙遠了。
儘管如此,儒家文化的擔當天下、以民為本,文人為官的高風亮節、博大胸懷、廣闊視野,仍然是非常寶貴的民族遺產。蘇東坡這樣的官員,放在任何時代都是好官的楷模。
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看也有問題。我不知道聖人的心裡究竟是怎麼想的,反正聖人之言,是容易教人把“利”與小人相連,將“義”和君子相連。君子固窮也罷了,他還要視富貴如浮雲。聖人為了防範人性惡講了很多格言警句,卻顯然妨礙了人性的自由伸展。竊以為,對人性是有遮蔽的,擋住了後來的思想家們投向慾望的視線。漢儒、宋儒、明清諸帝又強化這個遮蔽。慾望未能受到辨認和追問,反而導至一輪又一輪的慾望氾濫。
孔子輕視女人,設男女之大防,影響惡劣而深遠。即使在唐朝,即使是名流顯貴的老婆也很難留下她們的姓名。直到曹雪芹,才發出一聲驚破千年的棒喝:女兒是水做的,鐘山川之靈氣,鬚眉男子是濁物!曹公筆下的奼紫嫣紅的金陵裙釵,照亮幾千年。
李澤厚老先生的《論語今讀》,我反复看,受益非淺。不過,利和慾兩個層面,孔子的言論就擺在那兒,憑老先生怎麼強為之辨也顯得難圓其說。
仁義道德的宏大敘事,長期壓制慾望和功利,而文人幾乎都是儒者,自己受影響,又去影響更多的人,擴大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的覆蓋面。宋代,商品經濟發達了,市民社會興起了,但文人重義輕利的意識還是很頑固。士大夫中的傑出分子,確實能做到君子固窮。司馬光王安石,兩位名相,都不提倡消費的。當然,他們有針對性:針對官僚階層的驕奢淫逸。辛棄疾這樣的豪放人物,北方漢子,對南方大城市的商品貿易是頗有微詞的。蘇東坡則發出感慨:“處貧賤易,安富貴難。”東坡在富貴與貧賤之間反复折騰,將中國人的生命體驗從幾個方向推到極致,成為生命之絕響。文化大師們身體力行,始終保持向上的姿態,而影響卻是多方面的。在廣袤的民間,在從北到南的各類民風民俗中,錢、利、色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說出來。最典型的是戲台上的文弱書生,一談錢他就羞羞答答,一近色他就縮手縮腳,一抬腳他就很像唐僧……漢唐宋文人的血性野性不見踪影,且不說先秦雄風。看來是明清御用文人做了民間藝術的手腳,以道德壓人性,以官僚階層的趣味鎖定大小戲台:從內容到形式。官僚們盡可放縱,卻要讓天下百姓活得中規中矩。
中國的國粹魚龍混雜……
古代社會,對功利的嚴加防範可能是最大的遮蔽之一。這使中國人步入現代社會舉步維艱。對慾望的持續高壓使慾望扭曲變形,病態的人,病態的生活,在魯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揭示。不過歷史有慣性的。曾幾何時,我們經歷了大鍋飯和平均主義,狠批私字一閃念,農民賣幾根蔥子蒜苗都要東張西望、擔心市管會。及至國門洞開,經濟高速運行,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舉世矚目。與此同時,良莠不分的洋觀念也蜂擁而來,令人一時難辨好壞。受到壓抑的慾望在短期內強勢反彈,功利二字在商品大潮中膨脹開來,又形成新的遮蔽:價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威脅。更有甚者:連工具理性都避退三舍,讓位給非理性的慾望之舞。
慾望的收縮與膨脹,看來都不是好事。
我懷疑“現代”這樣的字眼,在其他國家的使用頻率不是這麼高的。 “現代”的呼聲分貝太高,“傳統”會鬱悶的。老嚷現代者,給人的印像是生怕傳統拖了他的後腿,必欲棄之而不顧。走極端的傢伙,則把數典忘祖當時髦……
現代與傳統不應該呈現二元分割的局面。支撐著這種分割局面的,乃是形而上學的主客體分離的思維模式。
而眼下,文化建設被提到了國家戰略性的高度。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為此歡呼。
綜合上述,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是文人的智慧通政治智慧,所謂文治武功,文是首要的。文以載道,文道合一,道是意識形態和普適價值。從屈原到梁啟操,文人侍讀、做太傅、修國史、變法度,形成蔚為大觀的傳統。歷代高士、謀士、名相、名臣,都具備很好的人文素養。像張良,把兵家道家儒家的智慧高端融合;像諸葛亮,貫通了儒、法、兵、道、墨等源自先秦的諸子智慧,游刃於異質性的境域,諸學皆明亮:諸各亮。
二是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餘波未息,某些作家或學者,要么以媚俗的方式趨利,要么擺出大拒絕的姿態固守著象牙之塔。這趨利與拒絕,都是古人的不言利在當下的變式,前者易滑向低俗亂來怪叫,後者則可能趨於自說自話,讓驕傲變成驕傲本身,失去作家與世界之間的寶貴的張力區。豐富的內心總是指向世界的。所謂背向世界面向自己,弄得不好就流於孤芳自賞孤掌難鳴。
三是古代文人的奔官場情形比較複雜,文人有趨炎附勢;有清高,有脆弱:碰上小人庸人他就生氣了鬱悶了,轉身走掉,置事業於不顧。文人敏感,浪漫,情趣多,反正他有的是去處。官場污濁他就奔田園,人事混亂他就做隱士。所謂至情至性者,也常常是脆弱者,像歐陽修的易受傷,王安石的狷介不容人。文人活向真善美,活向政治理想主義,既創豐功偉績,又構築了“清高”這一道有著自保意味的心理防線,這兩方面的遺產都有待清理。清高,脆弱,發牢騷,撂挑子,耍嘴皮子……都有歷史慣性。
而歷代文人感天動地的,是他那擔當天下的超越性:超越他所屬的強勢階層,把深度關切的目光投向苦難蒼生。例子很多,值得專題研究。傑出文人都是百折不撓的血性漢子,不拿信念、原則與個性去做交易,他們是照出政客、小人、市儈嘴臉的明鏡。文人失意有前提。 “失意文人”這個流傳甚廣的詞組須重新考察。傑出文人的失意,倒是直接導至了生存境域的敞開、生命的強化、美感的橫呈。古代許多文人,如果他稍稍向君王或權貴讓步他就會得意的。然而他倔,流放、受刑、連累家族乃至身首異處血濺七尺,他不改其志。失意文人不失信念。歷史的長河中這是非常寶貴的品格。而古今官場,人文修養的缺席是不可想像的:齷齪之風將暢行無阻。
2
在審美的領域,古代文人的貢獻怎麼說都不過分。而這個“怎麼說”尚待深入和細化。在文化、文明大碰撞的世界性的格局中,我們的審美傳統需要再回首、再掂量。本文僅限於談一點感受。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思,是民間的男女之思。孔子這個著名短語,為民間的東西定了調。後世文人幾乎都向民間借力,汲取民間的各類精華。屈原未必尊孔,可他的作品與荊楚大地息息相通,同樣對文人有多重指引。孔子,老子,莊子,屈子,以“文”的方式化育著後世文人,滔滔源頭流向南北東西,繪出華夏的人文地理。
這個人文地理,具有特殊性、唯一性。
漢字漢語多歧義,有彈性,“內存”難以測量,更能訴諸審美直覺。邏輯性思維的不夠發達,倒給審美直覺騰出了空間。
不過到了近現代,尤其到當代,中國人的邏輯思維也比較發達了。這表明:在漢語中長大的人也能學好數理化,能搞科研經濟。漢語一度自卑、受指責,為時僅有幾十年,只是歷史的一個瞬間。現在漢語的抬頭已是不爭的事實,全球的漢語熱不消細說。
漢語中所蘊涵的價值觀正以各種方式輸出國門去,價值觀的“貿易逆差”可望扭轉。
漢語藝術,是華夏文明的核心價值之一。
屈原不能為楚國效力,生命力就轉向語言藝術,行吟詩人,苦吟詩人,至死和語言藝術同在。杜甫半生苦難,顛沛流離,卻幾乎每天寫詩,牢牢棲身於漢語藝術。蘇軾出川,陸游入川,舟車長驅幾千里,也幾乎每天寫詩。寫作究竟是為了什麼?僅僅為了減壓、放下生命的重荷嗎?
寫作的源始衝動中有減壓的成分,然而更多的,卻顯然是為生命增光添色。
藝術使人洞察人生。藝術把生存諸環節、人生各情態展示出來,為一切情緒賦形,為生存之境域、生活之境界賦形。
古今中外藝術家的本源性衝動高度一致。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杜甫的長詩《北征》中這開頭幾句,一來就攝人心魄。蒼茫問家室,它帶出的境界雄渾壯闊,不讓陝地之黃土高原,什麼畫筆能描繪、什麼儀器能精確測量呢?畫筆或鏡頭庶幾能表現出幾分神韻,儀器卻派不上任何用場。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杜甫這是自況。他又描繪李白:“落筆驚風雨,下筆泣鬼神。”
宋人形容東坡的詩詞:“如天風海雨逼人。”形容柳永則是:“二八嬌娘執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
李煜的愛、恨、哀、愁,柳永的羈旅情愁,李清照的輕愁濃愁……相同的愁字,不同的微妙賦形,帶出各自的命運特徵。而這些都是人類的的基礎情緒,漢語詩人們為它們永久賦形,散發著強烈的華夏文明的氣息。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二月春風似剪刀。”
“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欲將西湖比西子,淡汝濃抹總相宜。”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林沖雪夜上樑山。”
“意綿綿整日玉生香。”
“颯爽英姿五尺槍,暑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
嗬,真是美得!
我不過是隨手舉例。蒼海一粟而已。
老外們咋能不學漢語?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賞這些妙語妙境。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美是精雕細琢。美是展示最微妙的人生情態的差異。差異的持存帶動社會生活的多元化。
審美的強度,就是生命的、生存的高度。
行文至此,我們似乎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古代文人越是到了窮途末路,越能“詩窮而後工。”生存的落差,往往導至生命力的強勁反彈。讀魯迅我們悟出:漂亮而堅硬的鑽石般的文字乃是長期受力的結晶。
古代大文人,幾乎全是生存落差的產物。 “落差”是在文人返身打量落差的時候顯現為落差的。而打量意味著:持久而深入地看,看人事,看自然,看鬼神。 “落差”是看出來的。
深入地看,於是有了超越性,有了向上的生命形態。而深入的前提是能夠深入,這裡修身是關鍵:修道德之身,修審美之身,修悲憫之身。以白居易為例:他在京城做著高官,卻能學杜甫細看普天下的受苦人,不惜得罪那麼多的權貴,寫出直接干政的《新樂府》、《秦中吟》。他投向那風雪中又冷又髒的賣炭翁的目光是多麼深入。
當古代文人寫出他們的生命體驗的時候,這體驗就通向了任何人,將生命的強度帶給任何人。而傑出藝術的獲得有個前提:活得投入。活得投入的人才“有”生存之落差。陸游對唐琬長達六十年的懷念堪稱範例。深切的懷念源自深度生存。
古今人傑,沒有一個是淺表性生存、活得嘻皮笑臉的。
順便提一句:眼下具有病毒特徵的、嚷著要“娛樂天下”的淺表性生存快餐式生存,正迅速消耗著自身。我們日後要做的,只是跟踪殘餘病毒的轉移。這情形如同西方的“後現代主義”趨於式微,“新歷史主義”登場。
康德說:“美是無利害的愉悅。”
看見一朵花一片雲,人就會高興。這高興與生計無關,與功利無關。 “清風明月不用買。”
傳向千萬年的藝術精品,均與功利無關。
唐詩之盛和唐朝的以詩取士是有關係的,宋詞之盛與宋朝的文人主政也有關係。但不能說李杜蘇辛寫詩詞是為了取悅君王。文學的自主性自律性至少從就開始了,經由楚辭、司馬遷、兩漢樂府、魏晉風骨而自成浩浩江河,“流”出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驚濤拍岸三千年。雖有拍馬文字擾亂視聽,卻不足以撼動江河。即使是李杜寫給權貴的那些“幹謁詩”,誰在欣賞或模仿呢?
文學藝術的自主,就是審美的自主。
傑出的藝術,既不向權力場、也不向市場時尚尋求本質性的依據。中國古代文人,當他失意的時候他就得意了:得人性之意,得審美之意,得天地造化之意。
“文章憎命達。”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曹氏家族不敗,我們是讀不到的。
為什么生存的落差會產生經典的作品呢?簡單說來,可能是落差導至無窮的思索與激烈的感慨,強者在逆境中變得更為強大,理性感性野性,強力推進瞬間噴發,有如原子的裂變。曹雪芹那不可思議的感受力、感知力是在十幾年的創造性勞動中獲得的。曹雪芹在書寫中成為曹雪芹,重現了時光,重構了時光。紅樓殘稿吸引了多少續作者,而續作均以失敗告終。這大約是上帝拋給人世的一個隱喻吧?
唯有精神的強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記憶。曹雪芹是強悍者,惠及弱小者:中的吃和用,也瀰漫著揮之不去的精神記憶。而他究竟是如何重返、重現、重構時光的?至今無人能“解味”。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藝術形式的規律就是毫無規律,她像自然界一樣拒絕向人類知性給出她的本質。
“在自然背向技術之處,恰好隱藏著自然的本質。”
也許,在藝術背向意誌之處,恰好隱藏著藝術的本質。
而藝術和自然的本質就好比宇宙中的黑洞,只能靠環繞著黑洞的物質加以推測。黑洞本身不能觀察。
對人類的頂級藝術,我們只能抱著虔誠。當我們向杜甫、雨果、海明威或曹雪芹致敬的時候,會發現:這敬意無邊無際,怎麼“致”都不為過。於是我們說:哦,這便是虔誠了。
中國古代文人,是歷史給予我們的饋贈。三皇五帝早就沒了,唐宋帝國也灰飛煙滅,而傳統文化的甘露始終是甘露。今日誰能說:他比天仙李白、比地仙蘇軾活得更精彩更豐富呢?
文豪們屹立天地間……
審美藝術強化著感受力,提升著感知力。二者匯成思之力,使生命衝動朝著更高更強。前後《赤壁賦》是很典型的:蘇軾貶到黃州,一變而為蘇東坡,問宇宙,問山水,問歷史,問生死,問有限與無限……無窮的追問,問出千古名篇。這也是英國大詩人艾略特所講的“思想知覺化”。
藝術是生命衝動的表達,這表達又強化生命衝動。衝動無休止,藝術無止境。
尼采說:藝術是生命的興奮劑。
這話是說:藝術激發人感受生命的能力。不過興奮劑也可能變成麻醉劑,所以海德格爾決定性地往前跨了一步,在驚動全球幾十年的《藝術品的本源》中說:藝術是將真理設入自身。
思與詩天然接軌。藝術是對生命、生存的終極追問。
所有的藝術形式,本質上都是詩。
“充滿勞績,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審美不是生命的點綴,審美是生命本身。
正是在這個維度上我們才得以理解:為什麼人是窮到極點也要美的。安徒生筆下那個劃火柴的憂傷的小女孩兒,用一根火柴照亮了全人類的童話世界。而喜兒手上的那根紅頭繩,其審美價值、帶給窮家女兒的愉悅感,顯然大於豪車帶給某些靚女的“短暫開心”,靚女她得了豪車轉眼就索要豪宅,她被“貪得無厭”這類生存情態鎖定,鎖死,因物化而固化,因算計型思維的濫用而反被這種思維所算計,她等於自尋晦氣,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可逆轉地降到動物的水平上,生活質量也就無從談起。 “豪車靚女”的生存論闡釋,大約是這樣吧。
我們重溫康德名言:美是無利害的愉悅。
順便提一句,上海茅惠芳女士演繹的舞劇《白毛女》,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音樂般的雪花,那雪花般的音樂,那純美的注視,那憂傷,那憤怒,那深山的孤苦,那浸透了人類的“基礎情緒”——愛恨情仇——的激情舞蹈……美得叫人欲說還休。
如果美是精雕細琢的話,那麼美就是“慢”的產物。慢工出細活。量化無佳作。佳作有如佳人,可遇而不可求。藝術創作的領域,強化意志是要扼殺感覺的。
我估計李白這樣的天才詩人也不敢說:明天寫它兩首好詩……
速度原本是個中性詞,眼下在時間的層面上趨於貶義詞。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驚呼:時間過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三五年!為什麼會形成這種不約而同的“心理時間”呢?我想了很久才悟出:是因為生活的快速運行丟失了細節,丟失了過程。算計型思維將生活分割成幾大塊,一刀切下,一眼看穿,粗暴抹去生活中極珍貴的模糊邊界,令時間加速,使生命縮短。人陷入刺激與無聊的惡性循環,卻看不見這個循環;單憑一己之力他也無法改變這個循環。生活的緩慢感是由生活的豐富性來決定的,反之亦然。韻味兒這種東西,嚴格排斥心浮氣躁。
活向刺激就是活向空虛,這是鐵律。
緩慢才“生長”豐富性;無欲方呈現多姿多彩的“欲之舞”。
舉童年為例,我們這代人的小時候是很豐富的,戲耍的花樣無窮無盡,事物都具有“上手性”,細節無限多。童年少年因之而緩慢,好像過不完。不希望長大的孩子才是孩子,他有自足的孩子們的感覺世界、遊戲世界。哪有什麼提前敏感的錢、權、欲!哪有山一般沉重的書包,哪有章魚(烏賊)似的吸空靈魂的網癮:一顆顆小圓頭被釘在了方形的顯示屏前。
生活的虛擬化乃是生命的虛無化。
電子遊戲的畫面會互相抵消,會導致失憶:不復有鮮活的童年呈現於中年暮年。它的平均化又抹掉個性差異,催生千人一面。電子遊戲最終所抵消的,是生活中千差萬別的敏感性。它的根據維繫在小小的“癮頭”上。癮頭是吸走生命的癮頭,它的擴張就是生命的收縮。
仔細回想一下,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個正常的小孩兒能同時敏感多少活生生的東西啊,意緒、印象、感覺,幾千種是保守數字。當時也沒人去數,去愚蠢,去消滅事物的“上手性”,去粗暴拆除日常生活的模糊邊界。
物種的多樣化,人的多樣化,生活方式的多樣化,決定性的字眼是“慢”,而不是快。
民間藝術,精英文化,生活意蘊,都是緩慢成形的,猶如自然界的所有奇觀。我們不能只見光速之快而忽視宇宙演變之慢。人類蹦蹦跳跳,也許上帝常發笑呢。
快與慢的辯證法,我們應當學著思考。
中國的審美傳統乃是幾千年點點滴滴積聚而成,她的價值是恆定的,永載教科書。現當代社會的一大功績,是讓這些珍貴的、不可替代的東西集中亮相。下一步,則是讓珍貴本身“顯現”出她的珍貴,她的驕傲與榮光;顯現出她對中國人的當下與未來的審美指引。
這個指引,是朝著傳統與現代的緩沖地帶,並最終消滅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分割。傳統在當下,贏得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重新成為傳統的契機。
上述種種,或可歸納幾條。
一是:審美的高度即生命的高度。審美觀照就是生存觀照。古代文人,與其說他們是先有生命體驗然後才去謀求表達,不如說他們是在表達中抵達了生命體驗。比如李煜,如果他不寫那些詞,他是沒有相應的生命體驗的。體驗之為體驗,有兩個運動方向:強化和細化生命的感覺。類似李煜的遭遇的君王,像陳叔寶、孟昶、宋徽宗,他們之所以不能成為李煜,就因為他們不能抵達李煜的生命體驗。而李煜的“抵達”的唯一途徑,乃是傑出的漢語藝術。相似的遭遇,迥異的體驗。沒有漢語藝術對生命-生存運動的高度提純,就沒有李煜的具有唯一性的生命體驗。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行珠簾閒不捲,終日誰來?”沒人來,但是詞句向李煜蜂擁時,生命之體驗來了。體驗具有“上手性”,遭遇則是“現成在手”。狗之將屠也哀嚎,卻嚎不出“亡國之君哀以思”。杜甫李白李清照曹雪芹,誰不是這樣呢?海德格爾讓歐美思想界為之折服的短語:“生存達乎語言”,也許包涵了這層意思。中國古代文人,在生存中達乎漢語。語言高於生存。或者說,生存是在語言的彈性框架內展開著的生存。這個現象學式的顛倒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回到事物本身”成為可能,使語言藝術與生命體驗的二元分割有望消彌。
曹雪芹的生命體驗,是經由來抵達的。 “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辛苦的人多的是,為何曹雪芹的辛苦不尋常?因為他把他筆下的每個漢字都變成了血滴。不寫,哪有相應的生命體驗?沒有曹公持續而深入的回望,哪有那些多層次的、質感如此之強的紅樓生活場景?而回望是在語言藝術的層面上才得以展開。
中國人是漢語思維者的同義語。
竊以為,世界性的“現象學運動”將在漢語中覓得一塊理想的基地。
二是:循序漸進環環相扣的審美傳統,對應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姿態,互相影響,彼此融合。生活方式的形成,少則幾百年,多則上千年。社會生活的連續性,類似自然界的連續性。切斷這種連續性是不可能的,人類自斷根係等於自掘墳墓。欲摧毀傳統者只不過是小打小鬧,或不無價值,或純屬胡鬧。社會形態變了,價值體系卻會傳承,審美傳統會穿越所有的社會形態。古代文人將生存各環節、各情態淋漓盡致展示出來,深入我們的民族集體潛意識,影響知性與感性。而清理這個潛意識的巨大工程尚未全面開工。為什麼孔子莊子屈子唐宋詩詞讓我們感到如此親切?這樣的課題有待展開。蘇東坡若能沿時光隧道出現在杭州或北京的街頭,肯定會受到萬民鼓掌歡呼的,他就像所有人的親人。這究竟是咋回事兒呢?李白李煜在互聯網上的相關詞條有幾百萬……
三是:中國歷代文人提升了民族的感知能力,為各種微妙的場景、情緒、情感賦形,為“看不見”的人生氣象、精神境界賦形。其抵達的廣度與深度,肯定是世界第一。哪個小山村沒有幾個讀書人呢?東坡貶海南辦起了學校,海南就破天荒出了進士姜唐佐……如今,凡是在漢語中長大的人,無論他走到南極北極,辨認另一個中國人是非常容易的:一說水滸紅樓三國西遊,很快就心意相通笑逐顏開了。漢語藝術攏集著炎黃子孫。由此可見,從屈原到魯迅的數以百計的傑出文人,也提升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這個豐功偉績,給我們留下了不可測量的闡釋空間。
末一層,是審美藝術的非功利性。古人寫詩文,主要是表達、提純體驗,使生存朝著更高,使生命朝著更強更豐富。如果藝術有一點規律的話,這可能就是規律。寫詩不是衝著官場的,毋寧說,詩人寫好詩反而有礙他的仕進。詩意自足,文學自律。自足與自律是慢慢形成的,根深導至葉茂,兩千年強勁伸展。司馬遷寫《史記》,是背著漢武帝幹的。陶淵明寫給誰看呢?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江西鄉下的一群素心人,年復一年樂此不疲。非功利才有藝術精品,再如曹雪芹,寫作使他全家受窮。支撐著曹公的,是不可遏止的生命衝動,審美衝動。詞語的運行就是生命衝動。
審美也包括審醜。既然是“審美觀照”,就得觀照世間萬物。
生存的巨大落差,反而使文豪們贏得審美之境。
近現代西方的科技進步,也是非功利的。第一流的科學家只對他的研究對象感興趣,他要窮盡這對象,僅此而已。他不會輕易離開自己的實驗室跑出去亂轉、腦子裡塞滿功利。這個有利於基礎研究的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
藝術,生活,感覺層面的東西是至關重要的。陳嘉映先生近年的隨筆集,書名叫《從感覺開始》。這裡邊饒有深意。現代人邏輯思維發達了,一個明顯的結果卻是:生活趨於概念化,世界趨於圖像化(圖像不是指影像),“可感”成了問題。從概念返回感覺的原發地帶是艱難的。這裡有雙重遺忘:對感覺豐富性的遺忘,和對這種遺忘本身的遺忘。
老實說,局面不容樂觀。
功利是意志層面的東西,而意志又有封殺感覺的功能。意志再變成強力意志、求意志的意志,感覺就會呈現一片蕭條。為什麼這些年重拍的幾十種影視經典全都比原作差了一大截呢?憑藉這個極端例子恰好可以展開我們的追問:對文化產業化的追問。
而古今的優秀作品都是能夠激活感覺的。古人的作品,由於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倒比當下的許多作品更能抵達今天,直指明天。唐詩宋詞能傳一萬年嗎?我們不禁要問:為何能傳一萬年?能傳一萬年的“這種感覺”究竟有哪些原發之物?
從感覺開始的一個有效渠道是:從好作品開始,慢慢找回感覺的豐富性。僅憑一位李太白,那裡有多少不可測量的偉大感覺啊。
感覺的豐富性永遠是生活的豐富性的前提。
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該是找回感覺的世紀吧。
3
文人與自然的話題,不可能是個輕鬆的話題。
包括老莊在內的古代文人,無一例外是要讚美自然的。古人畫山,山大人小,往往小到看不見;畫鳥獸魚虫,不見人影。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初度月黃昏。”詩中只有情緒,人是不露面的。人在不露中“露”著,露出他的謙遜,他的虔誠。詩人從來就不是“面對自然”,他在自然之中,是大自然的一個謙卑的成員。他讚美鮮花,讚美一條魚的游動、一灣水的流走,並由此生髮出許許多多。 “花退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東坡這個名篇,眼下有些人偏往性的方向讀,一味猜想青杏小與王朝雲的性瓜葛,是頗能代表一部分人的閱讀心態的。
慾望太盛時,詩意要溜走。
花退殘紅、燕子飛、綠水人家繞,是“落實”到王朝雲青杏般的小乳房麼?如此解讀東坡,哪裡還有東坡。那些個掃來掃去的慾望之眼,看見的男人全是西門慶。
我寫曹雪芹的時候有個擔心:擔心大學校園裡的一些讀者,可能難以分辨賈寶玉和西門慶的巨大差異。金錢觀念入侵校園,慾望邏輯劫殺美感。賈寶玉的眼睛是豐富的,是審美之眼悲憫之眼憤怒之眼追問之眼,西門慶的眼睛則是標準的動物眼。動物是沒有“環境”和境界的,它的環境只不過是身體的延伸。審美的廣闊境域,乃是人類文明的結晶。一條狗它能欣賞大觀園裡的群芳諸艷嗎?
審美之眼是說:放出去的目光呈輻射狀,多層次,多角度,深入而又細膩,有如春風吹拂,有如夏雲崢嶸,有如秋高氣爽,有如冬陽普照……
這樣的眼睛當然是修煉而成。
曹雪芹對“鮮花之為鮮花”是十分敏感的,梅花、菊花、梨花、荷花、牡丹花、芙蓉花、海棠花……“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海棠詩社,菊花詩社,曹公筆下好詩如潮。 “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以清爽女兒的口吻寫詩,曹雪芹是能夠獨步古今的。以美好女性的紛呈對應百花爭艷,曹公做到了極致。於是才有花的凋零,才有女孩子的辛酸淚,才有命運的悲涼悲愴的曲線……
自然與人事,在曹雪芹的眼中是高度融合的。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說不清這是鮮花的感受還是林黛玉的感受,能說的是:二者俱貼切。
將人事化入自然的無限律動,中國古代的文人獨步全球。
中國文人激活了中國山水,例子俯拾即是。李白的那雙亮晶晶的眼睛甚至激活了月球上的環形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李白的名字為環形山命名。西方大詩人無此殊榮。關於月亮,李白造詞之多也是全世界第一。
如果地球是個生命體的話,那麼月亮也是有生命的。只是地球月亮的“生命形態”,無限高於人類的理解力。人類是進化過程中的人類,不可能具備“終極理解力”。茫茫宇宙之中,連地球、連太陽係都是滄海一粟,何況是人類。人類既偉大又渺小。人類的偉大除了一系列的創造之外,還在於:他是既知偉大又懂得渺小,懂得人類在宇宙中永遠的微不足道。
對人類文明來說,月亮首先是月亮,然後才是月球。而後者的亙古荒涼的月貌倒指向宇宙的無窮神秘。美國有個宇航員,回到地球上就做了傳教士。眾所周知,霍金先生對宇宙大爆炸之後的勻稱佈局感到無比驚訝,他是傾向於相信上帝的。
人類已經為“宇宙式的傲慢”付出了沉重代價:災難性氣候頻發,地球對棲息在她身上的這個物種越來越“不耐煩”了。
而中國古代文人對自然的審美姿態,則越來越成為普適性價值。審美姿態是說:人並未將自然處理成可支配的對象,不將自然視為“存貨”。人與自然的這種和諧意味著:人不欺天,天不狂怒。天是幾十億年的那個天,人是幾千年走過來的這個人,天人合一,天在上人在下,天為尊人為卑。人幹蠢事兒,老天爺要懲罰的。
“自然”一詞深藏著祖先智慧:是她本來所是的那個樣子。是河流的天然彎曲使河流成為河流……自然有生命,這生命的法則掌握在她自己的手裡,她不能被支配,被掌控。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詩人的驚奇,詩人的意之所向,是永恆的自然之謎和時間之謎。並且,通過這一決定性的驚奇和意之所向,使人融入到自然與時間之中。驚奇的拋出與反彈是永恆的,如若不然,我們今天是領悟不到李白的驚奇的。
現象學的研究表明:對象之所是,取決於投向對象的目光。
古代文人投向自然的目光乃是謙卑的目光。他被神性與詩意所包裹,他對宇宙萬物及其美妙循環保持著他的“源始驚奇”。他傾聽,他環繞,他漫步,他打量,他欣賞,他驚嘆。
然後他書寫,為自然的千姿百態命名。如同他為人事心境之萬千曲折命名。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詩意不消耗能源。詩意是用之不竭的精神能源。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餘。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屈原在漢語中抵達了他和湘夫人的邂逅。他與荊楚大地之神靈同在。我們閱讀屈原,亦與神靈同在。
詩人是自然的溫柔情人,不會去算計她、粗暴地掠奪她。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
細膩的描繪,雄渾的氣象,詩心乃是自然律動的同義語。這裡沒有主觀的感受,細膩或雄渾也不是客觀的東西。書寫者與他的書寫之物是融為一體的,沒有對象化思維,沒有主客觀對立。
“意識總是某物的意識…”
胡塞爾晚年致力於“生活世界”的研究,海德格爾力倡“詩意棲居”,旨在扭轉技術主義消費主義的氾濫對人類的嚴重傷害。西哲們的強勁之思,與中國文人的審美觀照是相通的。
改造自然是必要的,改變自然是愚蠢的、危險的。
希望經濟的全球化不要惹發災難的全球化……
近日看央視國際新聞,美國某地的氣溫竟然在幾個小時內狂降二十八攝氏度。氣候要殺人。英國的科學家們向來是很關注氣候變化的,他們都暈頭轉向了,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可以確定的是自然的報復,難以確定是自然報復的方式、規模和速度。
今年中國南方的大雪災令人費思量。
我熟悉的川西壩子,曾經是河流清澈繁星滿天四季分明,眼下河也枯了水也髒了,星星也不大看得見了,隆冬就像陽春,蒼蠅蚊子亂飛……有時候想念一條兒時的“丁冬”小溪,想得心疼。而城裡的許多人年復一年變著花樣打牌吃飯,誰在仰望天空、俯察大地?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
“瓦屋寒堆春後雪,峨眉翠掃雨余天。”
一千年前的蘇軾是這麼描繪的。
我們崇拜著蘇軾,蘇軾崇拜著陶淵明。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陶淵明是中國的頭號鄉村詩人,他帶頭激活了中國的鄉村之美,杜甫、王維、蘇軾、陸游、楊萬里、江白石、辛棄疾…都是追隨他的。千百年來的中國田園之美,五柳先生居頭功。
是他向我們隨意指點:房前屋後皆風景,一草一木也關情。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心有多遠?
心之遠在切近,在周遭: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陶淵明是將人事的曲折化入自然的典範。真,善,美,三位一體,縱情撲向自然的懷抱。
什麼“隱逸詩人之宗”,真是奇談!
唐宋詩人這麼追隨他: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問君為何居此山,笑而不答身自閒…”
“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國的鄉村佈局就是審美佈局。
而鄉村之為鄉村,乃是城市的參照。
鄉野,鄉土,鄉村,這些簡單的漢語詞彙向我們訴說著多少美妙。我們多姿多彩的審美傳統,穿越時光抵達今天,緊緊環繞著、包裹著這個“慧核”。城市有許多美好,創造著財富和榮耀,卻也製造慾望與無聊的大面積循環。城市製造慾望,鄉野消解慾望。英國的鄉村、法國的鄉村、德國的鄉村、俄羅斯的鄉村……歐洲的城鄉格局真令人心動。
這心動源於我們固有的審美內核:鄉野。
偉大的五柳先生,深深懂得動植物的“朦朧的欣悅”: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辛棄疾則感嘆:“一丘一壑亦風流。”
小路、田埂、拱橋、竹籬、野花、飛鳥、黃昏、夕陽、雲彩、月亮、星星、炊煙、麥苗、稻浪、山巒、平原、草場、溪流、湖光、雨滴、霧靄、瑞雪、蛙聲、雞鳴、犬吠、人喧……
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嗡嗡嗡”的油菜花……
所幸這些漢語中的美詞,尚未退出我們的視野。
而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顯然不是為了消滅這些美詞。
早在若干年前,費孝通先生就強烈呼籲:鄉土中國應當成為城市中國的參照!
中國的鄉村不僅意味著十八億畝耕地,她更是一個巨大的審美符號,民風民俗的符號。她以其自然輝映城市,以其樸拙挑剔城市,以其廣闊的酥胸包容城市。
城市與鄉野,相異而相融。
曾幾何時相異凸顯,城市對鄉野翻著白眼斜眼。現在是到了再度融合的時候了,彼此青睞,城鄉共榮:指向高空的鋼筋水泥向遼闊而鬆軟的、生機勃勃的大地致敬。
每一個長居都市的中國人都有類似體驗:城裡樓裡待煩了,鄉下走一遭,瞧瞧風是怎麼吹的,草是怎麼綠的,山巒是怎麼起伏的,麥浪是如何翻滾的,鄉親是如何串門的……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鄉野之樸拙收縮慾望之膨脹。
慾海無邊,回頭是岸。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這一節就不用歸納了吧。
下面是本文的結束語。
古代文人有品讀前輩的傳統,歷朝歷代,閃爍著真知灼見。有三言兩語的,有長篇大論的。從孔子刪詩、王逸注《楚辭》,到《漢書.藝文志》,到《文選》、《詩品》、、《避暑錄話》、《苕溪漁隱叢話》、《香山詩話》、《六一詩話》、《東坡志林》、《容齋隨筆》、……曹雪芹有《廢藝齋存稿》,可惜已不存,而中有黛玉湘雲寶釵的精彩詩論。現當代的詩論、文論則更多更廣泛更系統。可見品讀文化先賢是延續華夏文脈的方式之一。
筆者品讀起於屈原迄於魯迅的十八位文豪級的先賢,內心始終惴惴不安。
我能直接瞄準中國文人的生命衝動麼?能提取他們的生命精華麼?能把活生生的傳統文化帶到當下麼?
而帶到當下的前提是要辨認當下。
不知今焉知古?
文化先賢們挺有意思,一個個活得十分帶勁。他們的生命形態、生存方式、生存向度值得研究。而用理性思維去把握生命衝動往往不得要領。也許非得動用直覺不可。直覺是理性感性未曾分割的混成態,具有原初性。直覺這東西難以捉摸,似乎只在它的投射之物中才顯現出來。猶如運動員的敏捷身手,離開運動場則不能展示。靜態的指標只能作參考。
人文領域,不宜作靜態分析。
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是什麼》一文中指出:“數學認識具有精確性之特徵,而這種精確性並不就是嚴格性。向歷史學提出精確性之要求,就會與精神科學的特殊嚴格性之觀念相抵牾。”
精神科學的特殊嚴格性,尚待我們思考。有一點是明確的:決不能向精神科學提出精確性之要求。提這樣的粗暴要求將導致精神科學的萎縮。
我有一些朋友常發疑問:為何活得那麼精彩的那麼多古人,到了課堂上就乾癟乏味了呢?歷史課,語文課,乏味太多。
課堂上的模式化標準化,妨礙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
而由於歷史的原因,古典文學的研究也存在著條條框框。
寫古代人物,如果沒有相似的價值取向或生命衝動,是要碰上故紙堆的。故紙堆它就像迷魂陣……
歐美的傳記類作品是非常迷人的,幾百年興盛,為文化的傳播、為文明的連續性作出了一份特殊的貢獻。
我們尚須努力。漢語藝術為我們提供了精神家園,這家園中的寶物尚須清點。
冷靜思考。熱烈洞見。
華夏文明的進程中,也許“哲學”這棵萬樹之樹長得不夠根深葉茂,未能繁衍出西方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可能是由漢語的特殊性所決定的。也許漢語更能訴諸直覺。也許漢語更能訴諸審美直覺。
孔孟之道統攝古代社會近兩千年,而道統的闡釋者傳播者實踐者都是廣義上的文人。儒學史學文學老莊之學,以及稍後的佛學,常常在一個文人的身上融為一體。文人之所謂修身,是集合了諸多元素的向上運動。儒道釋構成了文人-文官的完整的進退體系。用辯證的眼光看,退是進的退,包含諸多變式,比如以退為進(隱於江湖)或以進為退(吏隱);比如淵明式的干淨利落的“退”,會在歷史的張力中亮出瀟灑。
文人都要去做官。做官的大都是文人。這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十分罕見。這是華夏文明的特殊性。
古代社會的主流價值體係是由文人來提供的。這個體系的運行總的說來也是成功的,不然不會維繫兩千年之久。 “五四運動”以來,對這一體系的質疑與解構,在今天看,可能是以“反運動”的方式歸屬於這一運動。孔子與魯迅的對峙局面有望在更高的層面中得以融合。
差異構成歷史的張力。差異卻不是斷裂。
今日和諧社會、和諧文化的戰略指向乃是順應了歷史潮流。我們為此甚感欣慰。雖然前行之路從來就是坎坷不平。
我們的文化譜係是清晰的,清晰利於發力。我們的文化基因是優秀的,能反觀自身、能眺望並吸收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
“今天”贏得了歷史性的高度。
走向未來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在這個歷史性的高度上回歸了。這多麼值得歡慶。
回歸將是全方位的,到處能聽到傳統文化價值重估的聲音。我們的傳統價值觀正以各種形式輸出國門去,不卑不亢,“來而不往非禮也”。而這種不卑不亢的平和心態,真是來之不易。
現在我回想童年時代對科學家和文學家的嚮往,感到蠻有趣:“嚮往”猶如種子,開出了幾朵小花。我讀著“咱們的古代”並且想入非非,覺得張飛或宋江遠比眉山街頭的行人來得更實在。上高中我開始偏科,數理化常常很難及格。這使我的邏輯思維成了問題。當哲思以胡思亂想的開端黑洞般吸引我,我宿命般轉向了哲學,尤其是西方哲學,但是,讀得艱難。通常花幾年時間才靠近一本書。我領略了思想的密度、語言的密度。二十多年來我幾乎不間斷地爬著“西山”,老實說,這座“西哲之山”究竟有多高,我至今是不清楚的。更要命的是:我永遠也不會清楚。不過爬山爬了多年,總算對高度有一點感覺。點點滴滴的靠近與快步走近,究竟是不同的。而在“西山”之上,我驀然回首去打量“東山”,可能獲得了異質性的瞬間印象。由這印像生發開去,火花般的瞬間噴射得以在書寫中持存,顯現出“東山”上的諸多景觀。也許不乏新景觀。
時代也不同了。歷史形成的諸多遮蔽,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正云開霧散。這一層,是可作專題研究的。
對古代人物“原初地看”,在今天成為可能。
歷時一年半,我在編輯先生的高端催逼之下保持了強行軍的態勢。強行軍攏集了三十餘年的讀、寫、思。其實不用查太多資料:感覺和印象的緊急集合似乎更能撲向思索。這好比一場足球比賽,奔跑、迂迴、盤帶都是朝著臨門一腳。冷思考獲得了它的熱效應。而由於現象學-生存論的環環相扣的指引,我對事物的固化傾向盡可能地保持警覺。
思想與時間同構。時間與生活同構。
滯留於思想的原發地帶意味著始終保持生命的活力,這很難,這需要辨認形形色色的固化。生活之流,意識之流,固化乃是常態,連不識字的農夫農婦也很能固化呢。
思想是生髮思想的一種能力;思想的常態是“活蹦亂跳”……
玄思就到此為止吧。
太陽升起,太陽落下;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太陽又始終是那個太陽。古代人物能鮮活於當下,首先是因為他們都擁有巨大的生命力、能穿透歷史的生命力。他們與漢語同在,就等於和祖國山河同在,和歷史同在。如果文人是一種職業的話,那麼它也是一種關乎所有職業的職業。 “關乎……”為“超乎……”奠定基礎。這個涵蓋了哲、史、文的課題尚有待深入。
從孔子老子莊子屈子到魯迅先生,中國歷代文人實實在在是個百折不撓可歌可泣的群體,是傳承華夏文明的主力軍,是承受著家國苦難的勇士,是美的揭示者,是自然律動的傾聽者,是封建強權的反抗者,是生活世界的洞悉者——中國文人的生存姿態、生存向度,對當下的中國人明明白白是個精神指引。
而他們的歷史局限,則應當被同時納入視野。
人是不能活得鼠目寸光的。一味嚷嚷現實,直奔眼皮子底下,現實會產生位移,會收縮它的地平線。中國傳統文化特別講究虛能致實,無為而為。虛能致實是說:無形的東西規定著有形之物。語言的抽象規定著一切具象。語言是存在的家,“猶如雲是天上的雲。”
我們不可失掉我們的智慧祖先曾經有過的深邃目光,不可失掉這目光所抵達的廣闊的地平線。
價值的天空就像自然的天空一樣需要珍視。我們已經痛苦地發現:哪怕是修補一小塊價值的天空有多難。
“生活意義之網”若是拆成了碎片,每個人都會受傷。
小康社會,不僅是物質層面的。精神健全同樣是重中之重。
回行者能夠前瞻。回行幾千年能前瞻多少年呢?
回行的足音將以何種形式踏響未來呢?
歷史有慣性的,對文化先賢們的種種遮蔽今猶存焉。讓歷史之星空中閃耀著的恆星,去塵埃,明亮於當下,照耀著未來,尚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開。
工作是嚴謹的,工程是浩大的,眾多勞動者的手共同聯接著千古文脈與血脈。
“品中國文人”這個系列,僅僅是一己之粗淺開端。
2008年2月21日元宵佳節,改定於四川眉山之忘言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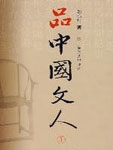
品中國文人
刘小川
雜文隨筆
類別- 1970-01-01發表
-
296088
完全的
© www.hixbook.com
按“左鍵←”返回上一章節; 按“右鍵→”進入下一章節; 按“空格鍵”向下滾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