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心:慶祝的藝術
我們訓練兒童去集中(focus)思想、去專注(concentrate),因為沒有專注,他將來就不能應付生活。生活要求這樣,頭腦必須能夠專注。但是,一旦頭腦能夠專注以後,它就變得很少有覺知了。覺知(awareness)意味著有意識(conscious)但並不集中在一點的頭腦,覺知是對正在發生的一切的一個意識(consciousness)。專注是一個選擇,它屏棄了專注對像以外的一切東西,它是一個狹窄化(nar-rowing)。如果你走在街上,你就必須窄化你的意識才能走路。你無法經常地覺知到正在發生的一切,因為如果你覺知到正在發生的一切,那麼你就變得無法集中。所以,專注是需要的。頭腦的專注是生活——生存和存在的一個需要。那就是為什麼每一種文明都以各自的方式設法窄化兒童的頭腦。
兒童從來是不集中的,他們的意識向四面八方敞開著,任何東西都在不斷地進入,沒有什麼東西被屏棄。兒童敞開著一切感覺,每一種感覺都被納入到他的意識中。有太多的東西在進入!那就是為什麼他們是那麼搖擺不定、那麼不穩定。兒童的還沒有被制約(unconditioned)的頭腦是一個流動——一個感覺的流動。但是,如果頭腦是這樣的狀態,那麼他將無法生存。他必須學會窄化頭腦,學會專注。
頭腦一旦狹窄化了,你就會變得特別意識到某一樣東西,而同時,你對其他事物毫無意識。頭腦窄化得越小,它就越能取得成功,你會變成一個特殊人才,變成一個專家。但是,整個事情就會是:你知道得越多,你的意識就越少。
狹窄化是一個生存性的需要,沒有人要對此負責。只要生命存在,它就是必需的,但是它是不夠的。它是實用的,但是僅僅生存是不夠的,只求實用是不夠的。因此,當你變成一個功利主義者而窄化了你的意識,那麼你就屏棄了你的頭腦本來有的許多能力。你沒有使用一個完整的頭腦,你只是在使用其中很小的一個部分,餘下的大部分就會變成無意識。
其實,意識和無意識之間沒有分界線,它們不是兩個頭腦。 "意識的頭腦"是指在窄化過程中使用的那一部分頭腦,"無意識的頭腦"是指被忽略、被忽視、被關閉的那一部分頭腦。這就產生了一個分割、一個分裂。頭腦的那一大部分變得與你疏遠了,你變得同你自己疏遠了,你成了你自己的整體(totality)的陌生人。
那一小部分被認同為你的自我,其餘的則都不見了。但是,作為未曾發揮的潛力、未曾利用的可能性、未曾經歷的冒險,餘下的這個無意識部分將永遠在那裡。這個無意識頭腦,也就是作為潛力、沒有使用過的頭腦將一直同有意識的頭腦作搏鬥,所以,人的內心始終存在著衝突。因為無意識同有意識之間有分裂,所以每個人都處在衝突之中。只有當潛力、無意識被允許像花一樣開放時,你才能體會到存在的極樂,否則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的潛能的主要部分得不到實現,你的一生將是一個挫敗。那就是為什麼一個人越是追求實利,他就越得不到滿足,他就越沒有喜樂。一個人的生活態度越是功利主義,過著越是忙碌的生活,他就活得越狹隘,他就越得不到狂喜。在功利世界中用不上的那部分頭腦已經被拋棄掉了。
功利的生活是需要的,但是它的代價是巨大的:你失去了生命的歡樂。如果你的潛力能全部開花,那么生命就會變成一個歡樂、一個慶祝,那麼,生命就是一個慶典。所以我一直說,宗教就是把生命轉變成一個慶祝。宗教的層面是歡樂的層面,而不是功利的層面。
決不能把功利的頭腦當作全部的頭腦,不應該為了它而犧牲掉那餘下來的更大的頭腦。功利的頭腦決不能成為目的,它不得不在那兒,但是作為手段的。餘下的另一部分,更大的、潛在的部分必須成為目的。那就是我所說的宗教的態度。帶著非宗教的態度,那麼,商業化的頭腦、功利的頭腦就會成為目的。當它成為目的時,無意識就不可能把潛力實現出來,無意識將被拒絕。如果功利的頭腦成了目的,那就等於是僕人在充當主人的角色。
理智(intelligence)、頭腦的狹窄化,是一個人生存的(survival)手段,但不是生活(life)的手段。生存不等於生活。生存是一種必需,是存在於物質世界的一種必需,但是它的目的總是要達到潛能的一個開花、達到對你具有意義的一切的開花。如果你充分實現了,如果你裡面沒有任何東西停留於種子的狀態,如果一切都成了現實,如果你成了一朵盛開的花,那時,也只有那時,你才能感受到極樂、感受到生命的狂喜。
只有在你的生活中增加了一個新的層面——歡樂的層面、遊戲的層面,你那被拒絕的部分、無意識的部分才能變得積極主動而有創造力。所以,靜心不是工作而是遊戲。祈禱不是交易而是遊戲。靜心不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為平安、極樂而做的某件事情,靜心是把它自己當作目的的一種享受。
歡慶的層面是必須理解的最重要的東西,但是我們卻完全失落了它。所謂歡慶,我是指一個片刻接著一個片刻地享受來到你身上的一切事物的能力。
我們已經變得那麼受制約了,種種的習慣也已經變得那麼地機械,即使在沒有事要做的時候,我們的頭腦還是在忙忙碌碌。在不需要狹窄化的時候,你也是狹窄化的。即使你在做遊戲,你也不是在做遊戲,你也不是在享受遊戲。即使你在打牌,你也不是在享受它,你打牌是為了取勝。這樣,遊戲就變成了勞作,這樣,正在進行的事就不重要了,只有結果是重要的。
在事務(business)的層面,結果是重要的;在歡慶的層面,活動是重要的。如果你能使任何一個活動本身富有意義,那麼你就會變得歡樂,你就能慶祝它。每當你在慶祝它,那麼界限、種種狹窄化的界限就被打破了,它們不再被需要,它們被扔掉了。你擺脫了約束,擺脫了專注這個狹窄化的桎梏。現在,你不做選擇了,對來臨的每一樣東西,你都允許它。一旦你允許整個存在進入你裡面,你就和它合為一體了。那就會有一個共享(communion)。
這個共享、這個慶祝、這個無選擇的覺知、這個非交易性的態度,我稱之為靜心。歡樂就在片刻之中,就在活動之中,而不在為結果的操心中。沒有什麼東西需要去達成,因而,你能夠享受的就是此時此地。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解釋:我正在和你談話,如果我關心的是結果,那麼談話就成了一件事務,成了一個工作。但是如果我跟你談話而不帶有任何期望,不帶有對結果的任何要求,那麼這個談話就變成了一個遊戲。這個活動本身就是目的。那麼狹窄化就不需要了。我可以玩玩文字遊戲,我可以玩玩思想遊戲,我可以與你的問題玩玩遊戲,我可以與我的回答玩玩遊戲,那麼,它就不是嚴肅的,它是輕鬆愉快的。
如果你正在聽我談話而並不想從中獲取什麼,那麼你就能夠放鬆,你就能讓我與你分享,而你的意識就不會是狹窄的。那樣,它就是開放的。遊戲!享受!
任何時刻都可以是事務性的時刻,任何時刻也都可以是靜心的時刻,所不同的只是態度。如果它是無選擇的,如果你是在與它玩遊戲,那麼它就是靜心的時刻。
有待滿足的需要中有社會的需要,也有存在的需要。我不會說:"不要去製約孩子。"如果你讓他們完全不受制約,那麼他們就會變得粗野不堪,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生存需要製約,但是生存不是目的。所以你對製約必須能穿得上脫得下,就像衣服一樣,你可以穿上它出去辦事,然後回家把它脫掉,這樣,你才"存在"。
如果你並不認同你的衣服、你的製約;如果你不說"我就是我的頭腦",這並不困難,那麼,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地改變。但是如果你認同於你所受的製約,你說:"我的製約就是我。"而所有不是你的製約的東西都被否定了。你認為:"所有不受制約的都不是我,無意識不是我。我是有意識,是專注的頭腦。"這個認同是危險的,不應該這樣。一個恰當的教育是不受制約的。它只受一個有條件的製約:制約是一種實用的需要,你必須能穿得上脫得下。需要時穿上,不需要時脫下。在有可能把人教育得不和他的製約相認同之前,人類不是真正的人類,而只是受到製約和狹窄化的機器人。
要明白這一點,就是要覺知到那被剝奪了光明的大半部分的頭腦。覺知那大半部分頭腦,就是要覺知到你並不只是有意識的頭腦。有意識的頭腦只是一個部分,"我"是兩者,而那大半部分是不受制約的,但是它總是在那裡,等待著。
我給靜心下的定義是:靜心只是一個為跳進無意識而作的努力。你無法通過算計而跳進去,因為一切算計都屬於有意識,而有意識的頭腦不允許這樣做,它會警告你:"不要這樣做,你會發瘋的。"
有意識的頭腦總是害怕無意識,因為無意識一冒上來,意識中的一切平靜、清晰的東西都會被掃除掉,於是,一切將是黑暗的,就像在一個森林之中。
這就好像:你建了一座花園,四周圍了起來。你平整出很小的一片地,你種了一些花,一切都不錯,井然有序,幹乾淨淨。只是森林永遠就在旁邊,它不受控制,無法駕馭。花園一直在憂心忡忡之中。在任何時刻,森林可能會進來,那麼花園就會消失。
同樣,你耕種了頭腦的一部分,把一切弄得清清楚楚,但是無意識總是在它旁邊,有意識的頭腦一直處在懼怕之中。有意識的頭腦說:"別走進無意識中去,不要去看它,不要去想它。"
無意識的道路是黑暗的和未知的。在理性看來,它似乎是非理性的;在邏輯看來,它似乎是無邏輯的。所以,如果你要想用思考進入靜心,那麼,你就永遠也進不去,因為思維著的頭腦不會允許你進去。
這就成了一個悖論。沒有思考,你無法做任何事情;而帶著思考,你又不能進入靜心。怎麼辦?哪怕你這樣想:"我不要去思考",你這也是在思考。這是思考的那一部分頭腦在說:"我不允許去思考。"
靠思考是無法做成靜心的,這是一個困境、最大的困境。每一個求道者都會碰到這種困境,在某個地方,在某個時候都會出現困境。知道的人會說:"跳吧,別去想它!"但是你不可能不思考而做一件事,那就是為什麼一些不必要的方法被創造出來了。我說它是不必要的方法,因為只要你能不加思索地跳,什麼方法也不需要。但是你不會不加思索就跳的,所以方法還是需要的。
你可以去想那個方法,它能夠使你那思考的頭腦變得放鬆,但是不要去想靜心,靜心將是進入未知的一個跳躍。你可以藉助某種方法,而它會自動地把你推進未知。只是因為頭腦受過的訓練才需要這種方法,否則它是不需要的。
一旦你跳了,你會說:"這個方法是不必要的,根本不需要。"但是這是你回顧時的認識,你在事後才知道方法是不需要的。那就是克利希那穆爾提①說的:"不需要設計,不需要方法。"禪師們也說:"不需要努力,那是不必費力的。"但是,對於還沒有通過這道關卡的人來說,這是荒誕無稽的。因為人們說話的對象主要是那些沒有通過這道關卡的人。
①克利希那穆爾提(Krishnamurti,1895~1986):印度教成道大師。與神智學派首腦安妮·貝贊特合作創建世界明星社。 1969年以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奧哈伊主持克利希那穆爾提基金會。 ——譯註
所以我說,方法是人為的。它只是一個手段,讓你放鬆你的理性的頭腦,好讓你可能被推入到未知中去。
那就是為什麼我採用強烈的方法。方法越強烈,你那個會算計的頭腦就越不需要。方法越強烈,它就變得越完整,因為生命力不僅是屬開頭腦的,它也屬於身體、感情,它屬於你整個的存在。
蘇非派的苦修僧曾經用舞蹈來作為技巧和手段。如果你投入到舞蹈中去,那麼你就不可能保持理性,因為跳舞是一件很艱難的事,它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有一個片刻一定會到來,那是不用頭腦而在舞蹈的片刻。方法越有活力,越強烈,你就越能進入,理性就越不會在那裡。所以,舞蹈被用來作為一個技巧來推動你。在某個點上,不是你在跳舞,而是舞蹈會接管,它會接管你,你將被捲入那個未知的源頭。
禪師們採用過公案①的方法。公案是一些性質荒謬的謎題,它無法用理性來解答,你無法思考它。表面上,它又似乎可以思考出某些東西來。妙就妙在這裡。那些公案似乎可以讓人思考出些什麼來,於是你就開始去想,你的理性頭腦就舒服了,因為有一些東西已經給了它,要它去解決。但是那個東西是無法解決的,它的本質是不可解決的,因為它的本質是荒謬的。
①公案(koan):中國及日本佛教禪宗,特別是臨濟宗,用以訓練習禪者坐禪的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短句或問題。 ——譯註
有幾百個公案存在。禪師會說:"想想一個沒有聲音的聲音吧。"聽上去倒像是可以好好想想的:如果你努力思考,在某個地方,用某種方法,你總會找到一個沒有聲音的聲音,它好像是有可能的。然後,在某個點上——這個點是無法預料的、因人而異的——頭腦不管用了,它沒有了。你存在著,但是,頭腦以及它的一切制約都不見了,你就像一個小孩子,制約沒有了,你只是有意識的,狹窄化的集中沒有了。現在,你才知道方法是不必要的,但這是一個事後聰明,它是無法在事先說的。
沒有一種方法是因果性的,沒有一種方法是靜心的原因。正因為這樣,才可能有這麼多的方法。每一種方法都只是一個設計,但是每一種宗教都稱自己的方法為正道,而別的方法沒有用,他們都是用因果論來進行思考的。
水加熱後化為蒸汽,熱是原因,沒有熱,水就不會蒸發。這是因果關係。熱是蒸發的先決條件。但是靜心不是因果關係的,所以,任何方法都可以用。每一種方法都只是一個手段,它只是為事情的發生創造出一個情景,它並不引起它。
譬如說,這個房間的牆外是一望無際的開闊的天空,你從來沒有見過它。我可以同你談論天空,談論清新的空氣,談論大海,談論房子外面的一切,但是你都沒有看見過,你對此一無所知。你只是在笑,你認為我在編造。你說:"這一切美妙極了。你是個夢想家。"我不能說服你走到外面去,因為我講的一切在你聽來都毫無意義。
後來我說:"房子著火了!"這句話對你太有意義了,這是你能聽懂的。
現在,我不必對你作任何解釋了,我只要奔跑,你會跟上來的。房子並沒有著火,但是你一到了外面,你就不會再問我剛才為什麼說謊。意義就在那兒,天空就在那兒。於是你會感激我。說什麼謊都行。說謊只是一個設計,是把你帶到室外來的一個設計,它並不是造成室外的東西存在的原因。
每一種宗教都建築在一個謊言的設計的基礎上。一切方法都是謊言,它們只是製造出一種情景,它們不是原因。可以創造出新的設計,可以創造出新的宗教。老的設計不管用了,老的謊言不管用了,那麼就需要新的。把沒有失火的房子說成失火,次數一多就沒有用了,這時就需要有人創造出一種新的設計。
只要一個事物是另一個事物的原因,那麼它就決不會沒有用。但是陳舊的設計總是會沒有用的,需要新的設計。那就是為什麼每一個新的先知都必須同老的先知抗爭。他做的事和老的先知做的事一模一樣,但是他將不得不反對他們的教導,因為他必須否定那些已經變得失去意義而不管用的老的設計。
所有偉大的先知——佛陀、基督、摩訶毘羅①——都出於慈悲而創造了偉大的謊言,那就是為了要把你推出屋外。如果能通過某種手段能把你推出頭腦之外,那就是需要做的全部的內容。你的頭腦是牢籠,你的頭腦會要你的命,它是一種奴役。
①摩訶毘羅(Mahavira),即筏馱摩那,耆那教創始人,耆那教徒尊稱他為大雄,大雄音譯力摩訶毘羅。 ——譯註
就像我已經說過的,這種二律背反必然會發生,生命的本質就是這樣。你必須學會窄化頭腦,當你走出去時,它是有幫助的,但是在裡面,它是致命的。與人相處,它將是實用的;但是與自己相處,它將是自我毀滅的。
你不得不與別人、與自己共存。任何片面的生活都是殘缺不全的。與別人共存,你必須有一個受制約的頭腦:與自己共存,你必須有一個完全不受制約的意識。社會製造出了狹窄的意以,但是意識本身就意味著擴大,它是無限的。兩者都需要,兩者都應該被滿足。
能滿足這兩種需要的人,我說他是聰明人,偏向任何一個極端都是不聰明的,任何一個極端都是有害的。所以,要用你的頭腦和教養與世人一起生活,但是同自己單獨生活,不要用頭腦,不要用教養。把你的頭腦當作一個手段來使用,不要把它當作目的,一有機會,你就要從中走出來。每當你獨自一人,你就要從中走出來,擺脫頭腦。然後,慶祝這個時刻,慶祝存在本身,慶祝生命本身。
如果你能知道如何擺脫制約,那麼,僅僅活著就是一件值得大大慶祝的事。你能通過動態靜心學會這個"擺脫",它不是造成的,它會毫無原由地降臨於你。靜心會創造一個讓你進入未知的情景,漸漸地,你會被推出你那固有的、呆板的、機器人一般的人格。要勇敢一些!好好練習動態靜心,其他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的。這不是你做成的事,它將是一個發生。
你無法帶來神性(the divine),但是你能阻止它的來臨。你無法把陽光帶進屋子裡來,但是你能把它關在門外。從消極方面來說,頭腦大有作為;從積極方面來說,它一無所能。每一樣積極的事物都是一個禮物、一個祝福,它是降臨於你的。而每一樣消極的事物都是你自己的傑作。
靜心及靜心的一切方法能夠做一件事:把你從消極的阻力中推開,它能把你帶出頭腦的牢籠。等你出來以後,你會大笑。這麼容易就出來了,它就在那裡,只要跨出一步!可是我們一直在兜著圈子走,永遠踏不上這一步,踏不上能帶你到中心的這一步。
你一直在外圍兜圈子,重複同樣的事。但是,在某個點上,連續必須被打斷,那就是任何一種靜心方法所要做的。如果連續被打斷,如果你和過去變得沒有連續關係,那麼,那個片刻就是一個爆炸!就在這一個片刻,你回歸到了中心,你回歸到了你的存在的中心。那時你就知道了那一直屬於你的一切,你就知道了那一直在等待你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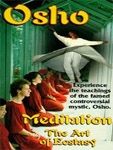
靜心:狂喜的藝術
奥修
宗教哲學
類別- 1970-01-01發表
-
159132
完全的
© www.hixbook.com
按“左鍵←”返回上一章節; 按“右鍵→”進入下一章節; 按“空格鍵”向下滾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