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閩交託我來寫他的的序,至少有一個堅強的理由:在他描述的那個鄉村,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從周歲起我就由當鄉村醫生的母親抱到這個叫“河田”的地方,一直到我讀初中一年級,才離開前往縣城。在某種意義上,我和西閩是真正的同鄉。我們操著同樣的方言,注視著同樣的鄉村風俗,他在本書中描述的所有鄉間景象,我都耳熟能詳。但很奇怪的是,在我大學畢業之後,我才得知有一個寫小說的同鄉,之前因為作為一位部隊作家的身份使他逸出了我的視野。
也許由於同樣的原因,西閩的創作才華也許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他是那種被稱為“性情中人”的人,個性自由狂放敏感,體驗極端,他只指出事實,從不講述思想。但他的作品常有一種直接從事實中逼近目的的能力,在本書中也是如此。這是一本描述死亡的書,這些死亡發生在鄉間,從而使每一種死亡事件變得詭異……作為死亡目擊者的少年黑子,他的黑色的眼睛記錄了所有的死亡事件,有的意義非凡獨特:李來福試圖餓死自己,最後累死了自己;王時常被打死,最後像一隻豬一樣被人捅入殺豬刀;王其祥則染上了狂犬病,像一隻狗那樣死去;王喜貴被凍死;賭鬼王老吉為贏得可憐的食物而打賭,活活被地瓜乾撐死;李遠新父親患了腸癌後為了讓家人快樂,一天吃一隻雞吃死;酒鬼丘土生掉到糞坑淹死;董春水死於雷擊;李文魁為了替兒子籌彩禮,自願死在兒子情敵的車輪下……也許你會對西閩如此密集地處理死亡事件而感到不舒服,但我讀完後,突然感受到另一種真實:即使這些事實不是真實的,但他寫出了另一種真實,即死亡本身是真實的。少年黑子自從失去了父親之後(這像是一種失去庇護的隱喻),就開始目睹各種各樣離奇的死亡,而且這些死亡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卑微性。我要說,這是真實的,因為這種活著的卑微性是真實的。在曲柳村,所有的人都離開了他的本質,荒謬的生存和荒謬的死亡是一回事。他們只是以死的方式來活著,這是多麼可怕的體驗。
書中有一些細節會把我突然打動:如王其祥得了狂犬病臨死前要和黑子“交個朋友”的最簡單最真誠的願望;老獵頭的宿命;黑子養父在洪水中救人而死;啞巴大叔在大饑荒時為了拯救全村人嘗野菜而死……這些死亡具有了崇高性。使得一本死亡之書加入了生命的重要內容。啞巴和盲妻無法交流的描述也充滿了隱喻。
但這仍是一本寫惡的書,死之書的另一種名稱就是“惡之書”,因為書中的人無法掙脫卑微而死的命運。這裡的惡被解釋為一種貧窮的宿命,所以,窮、惡、死在書中是一回事,它們有了因果關係。在少年黑子的視界中,他的鄉村記憶就是惡和死的記憶,當然也有愛和生命的印記,但相比之下,窮、惡和死的記憶更為深刻,連全書中唯一的一次動物的死亡——老牛的死——也是悲哀的。它的命運似乎是這個村子裡所有人的命運的寫照……螻蟻般存在。這就是黑子“無父”的宿命。
西閩用近乎話本的風格來展開敘述,使得本書可讀性很強。這也是他的一貫風格。但有些過於快速的敘述,令本書失去了某些隱忍的耐人尋味的意味。這是一個好題材,如果寫得更仔細會更好,但是這不會影響這本書成為重要的作品。西閩近年多寫恐怖小說,也因此而取得成就。但我認為這部卻表明了他的小說中的深切主題和體驗,是很值得期待的。用通俗的方式寫出大作品,有很多先例:如辛格的短篇集《卡夫卡的朋友》,因為他做到了最深切的主題和最通俗的俚語的高度統一,如果滑向馬爾克斯式的胡言亂語,則沒什麼價值。最通俗的表達和最奧秘的思想的結合,就是生命的本質,就像一棵樹長出了葉子一樣,不能只有樹的生命,也不能只有葉子,二者的割裂都是荒謬的。
我相信西閩會從本書的立場上繼續寫作同類型作品。他有兩個選擇:或者在通俗小說構架中加入更深刻內容,或者在所謂純文學作品的模式中加入通俗要素。如果他徵詢我這個同鄉的意見,我會說,這兩者是一回事。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的確還活著的話,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存在。因為死人才把靈魂和肉體分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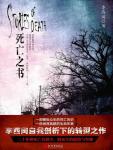
死亡之書
李西闽
驚悚懸疑
類別- 1970-01-01發表
-
141853
完全的
© www.hixbook.com
按“左鍵←”返回上一章節; 按“右鍵→”進入下一章節; 按“空格鍵”向下滾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