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子卿是我中學同學,也是我小時候玩兒伴。一個人到了四十多歲的年紀,再懶得交際,也總會結識下一些人的。在這些人中,也總會選擇幾個作為朋友的。人到中年,又有了中年階段的朋友,對小時候的玩兒伴,印像也就漸漸地消淡了。偶爾想起,不過就是一部分破碎的回憶,除了反芻一點兒從前的灰色童年的溫馨,實在也沒什麼別的親韻可言……
但對子卿,我卻很難忘懷。他彷彿永久地印在我記憶的底片上了。他彷彿是另一個我。替我在生活中追求另外的東西。因而使我簡直無法不關心他存在的種種情況……
我的父親,和他的父親,當年是一塊兒從山東從同一個小村里出走,“闖關東”來到東北的。當年他的父親十五歲。我的父親比他的父親小一歲,叫他的父親“俺哥”。如今的少年們之間,已很難有他們當年那麼一種雖非手足親似手足的關係了。人和人之間究竟能以什麼樣的關係相處,大抵也是由時代參予了決定的。
當年,我的父親和子卿的父親,“闖關東”的野心自然是向東北的城市傾斜的。然而東北的每一座大小城市當年都排斥這兩個身上一文不名,並且不諳世故的山東少年。最後他們不得不落腳在松花江畔的一個小漁村。它距離哈爾濱市五十幾里路。如果從江上划船逆流而上,距離會近不少。他們選擇那個小漁村落腳,證明他們當年嚮往有朝一日混進城裡的念頭是非常頑固的。儘管後來他們分別娶了那個小漁村里的兩個女人……
我六七歲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哈爾濱市裡的孩子了。子卿和我同歲。他也是一個哈爾濱市裡的孩子了。我們的父輩們的野心終於實現了。我們的母親們因此很崇拜他們。我們則更敬仰我們的母親們。因為她們從不曾在那些城市裡的女人們面前表現過絲毫的自卑。也因為那些城市裡的女人們並不敢隨意欺負她們兩個來自農村的女人。據說當年那些城市裡的女人們一向是很蔑視混進城裡的鄉下女人的……
嚴格地講,我們兩家其實並不能算在城市“裡”,而是住在城市最邊兒上的一條小街上。那條小街,好比城市這只巴掌上,靠近小拇指尖兒的一道最細的指紋。它的名字也起的低俗,叫“臟街”。也許並非它的名字,只不過被人們隨口叫,久而久之,就成了它的名字。至於它原本的街名,倒無人知曉了。
當年我曾問過母親:“媽,咱們這條街真叫臟街嗎?”
母親反問:“不真還假呀?”
我又問:“為啥叫臟街呢?”
母親也又反問:“你還覺得這條街不髒呀?”
那條街確實臟。很髒。街兩旁的住房,如果那也算“住房”的話,像吸了一輩子菸葉的老太太嘴裡七倒八歪熏黑了的牙。街一頭是下水道,整條街上家家戶戶的泔水都往那兒倒,經常堵塞。除了冬季,下水道口幾乎永遠淤著臭水。人一走過,蒼蠅便嗡地飛起一群。而冬季呢,周圍凍著一層層有顏色的冰。一層層冰的一種種顏色,使人瞧見了噁心。顏色恐怕也只有在那樣的情況之下,才會對人的胃起嘔吐性的刺激……
街的另一頭是公共廁所。是由碎磚、土坯、帶樹皮的木板和幾片油氈紙組合成的。年月久了,磚色已變了,如同東北人做醬的醬塊,而且是發了霉的。土坯呢夏天淋冬天凍,早已粘合成一整堵土圍牆了。而且傾斜著,似乎隨時可能塌倒。帶樹皮的木板就更不用說它了。朽得刮陣風都往下掉些朽木渣子。手指輕輕一捅就一個窟窿。只有頂蓋上的油氈紙,隔幾年由街道衛生隊負責換一次。街道衛生隊是沒錢改造那個廁所的。該做的也只能是隔幾年替它的頂蓋換一次油氈紙。他們一次也沒捨得用過新的油氈紙。所用都是從建築工地上收集到的廢棄油氈紙。結果是,雨天或夏季炎熱的正午,上廁所的大人們,總是在兜里揣一張舊報,蹲下後立刻雙手將報伸開在自己頭上。否則會有雨水珠兒或油氈的瀝青滴落在衣服上頭髮上。曾有女人的頭髮因而被瀝青粘住,用肥皂用鹼水洗了好幾次也洗不開的事發生過。最後她男人用了半臉盆汽油才幫她洗開……
“臟街”上的人都得上那一個公共廁所。那條街上僅有那麼一個公共廁所啊。這使它成了那條街上最公共的一個地方。經常可以看到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站在它的左側或右側聊天。是等著上廁所的人。上廁所的“高峰期”等在外邊的往往還不止兩個人。也有三個人五個人互相聊天一塊兒等的時候。其中準有一個人兩眼盯著廁所的人口,雙腳不停顛動,臉上不時作出齜牙咧嘴的古怪表情。是憋得非常痛苦快憋不住了的那位。這時候廁所就彷佛變成了頗詭秘的一個地方。出來一個人,進去一個人。出來的滿面歉意。進去的迫不及待。彷彿裡面有一位什麼神聖的人物,外面的人都是在期待著他的接見似的。當然過了“高峰期”,廁所外面沒人排著的時候也有。只一個人耐心可嘉地等待著的時候也有。如果沒人排在外面呢,剛上過廁所的人碰見了你,就會好心好意地告訴你——“還不快去上廁所?這會兒一個人也沒有!”對方呢,則會下意識地掉頭就往家裡奔,揣了手紙後,衝出家門,忙不迭地往廁所一溜儿小跑。那完全是一種條件反射。也許還有幾分“千萬別錯過良好時機”的心理在催促。而跑到了廁所跟前,他的泌尿系統或排泄系統每每提醒他完全是多此一舉。倘廁所外只有一個人在等著,倘他或她又不甘寂寞,便會跟廁所裡邊那位聊。這種時候,裡邊一句,外邊一句,一問一答的,拉家常嘮社會,情形很有意思。反正這條街上的人互相都認識,除非兩家有什麼芥梗,誰跟對方主動聊天,對方都是會表現出友善的配合熱忱的。當然,因為裡邊的人腹瀉或大便乾燥,等在外邊的人實在憋得不知拿自己怎麼辦才好了,於是相互口角乃至辱罵起來的不快事件也曾發生過……
我和子卿小的時候打過一架。就打過那麼一架。後來在廁所這個公共的地方言歸於好了。所以我對當年“臟街”上的公共廁所,至今保留著較深的、近乎懷舊的記憶。打架的原因極其簡單——某天我倆走碰頭,彼此撞了個滿懷。按說以我們兩家的關係,我倆是不該打起架來的。可是那一天我心裡不知窩了股什麼邪火,一直尋找機會發洩在某個人身上。子卿一向是讓我三分的。當時我認為發洩在他身上正對。彼此錯身而過之後,我突然衝口吼出一句:“你給我站住!”
他站住了,有些困惑地回頭望我。
我惡聲惡氣地問:“你幹嗎故意撞我?”
他說:“我不是故意撞你的。”
我說:“你是故意的!”
他說:“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說:“反正你撞了我就不行!”
分明的,他也有些來氣了,說;“不行能咋的?”
我一拳打在他鼻子上,打得他鼻子流了血。他一拳打在我眼眶上,打得我一隻眼亂冒金星……
事後我母親知道了這件事。狠狠訓了我一通。還罰我面壁跪了半個多小時。
母親指斥我:“知道錯不?”
我說:“知道了。”
又問:“為什麼錯了?”
我說:“不該先動手打人。”
“連子卿都打,今後你還不打遍這條街呀?你爸知道了,非揍你不可!你知道子卿他爸的腿是怎麼殘的?那是因為一次在一塊兒乾活的時候,出了險情,為了救你爸……”
我懂事以後,見到的子卿他爸就是個瘸子。整條街上的人都叫他“收破爛兒的翟瘸子”。母親說的事,此前我半點兒也不知道……
當天晚上,母親扯著我,去子卿家向他賠不是。子卿的家,比我的家還窮。只一間小屋子,床頭那兒就是做飯的鍋台。為了防止在做飯時床上的東西掉進鍋裡,在床頭和鍋台之間,豎立著一塊鐵板。那鐵板大概是子卿的爸收破爛收回來的。像這條街上所有人家的屋子一樣,子卿家的屋子也是沉在地下兩尺多的。這條街的地面原先高於人家的門坎。下雨的日子,雨水從街上往家家戶戶屋裡流淌。人們無奈,只好用爐灰墊自己的宅基和門坎。經年累月的,就用自己家裡掏出來的爐灰,漸漸地將自己家的房子埋了兩尺多。從此,家家戶戶的門坎倒是高出地面了,但家家戶戶的窗台卻矮了。坐在家裡朝外看,視線幾乎跟地面平行。倘正有人從窗前經過,只能看到那個人的腿。連膝蓋以上都看不到。
我母親扯著我邁進子卿家的時候,我沒料到他家的屋地比外邊的地面低那麼多,一腳踏空,險些連母親也帶倒,一塊兒跌入屋裡,幸虧子卿母親手疾眼快,及時扶住了我母親。子卿母親當時正做飯。更準確地說,是正往鍋裡貼餅子。子卿父親正給子卿補鞋。他和我一樣,沒有第二雙可換穿的鞋,也就只得老老實實坐在炕上,等著他父親替他補好那唯一的一雙鞋。
子卿母親扶了我母親一把,趕快又跨回鍋台那兒,一邊繼續往鍋裡啪啪地貼餅子,一邊問:“誰呀?”
子卿母親常年害眼病,視力很不好。
我母親就回答說:“是我呀,你老妹子。”
那時還沒來電。當年為了節約居民用電,要到晚上七點鐘才開始供電。鍋裡散發的蒸氣,瀰漫在小小的屋裡。子卿母親每貼一個餅子,要先往鍋裡吹一大口氣。吹散蒸氣,看清鍋裡的情形,她才不至於將餅子貼到鍋外,或將兩個餅子貼一起。在幾乎完全沒有光線的情況之下,子卿的父親居然還能補鞋,使我當時不禁暗覺奇異。
子卿母親往鍋裡貼完了餅子,蓋上鍋蓋,推開家門散盡蒸氣,接著在盆裡洗手。她一邊洗手,一邊問我母親:“老妹子,有事兒?”
我母親說:“也算有事兒,也算沒事兒,咋才做飯?”
子卿母親看了我一眼,不回答我母親的問話,卻很是有幾分不安地說:“你領著兒子來,我就知道為啥事了。子卿他爹已經把他揍過一頓了!”
我和子卿,都是隨著我們的父親們的山東人的叫法,稱他們為“爹”,稱母親們為“娘”的。我們是整條街上僅有的兩個不叫父母爸媽,而叫父母爹娘的孩子。別的孩子們因而叫我們“山東棒子”。我們的母親們雖不是山東女人,但由於嫁給了兩個正宗山東男人,也就早已接受並習慣爹娘的叫法了。
始終像個啞巴蹲在窗口補鞋的子卿父親,這時才鄭重地哼出一聲,嚴厲地說:“打架還行?不揍還行?再打架,非揍扁了他不可!”
光說了話,沒抬起頭。
子卿呢,則膽怯地往炕角縮去。
我母親說:“我可不是領兒子來告你兒子狀的。我是領兒子來向你兒子賠罪的。聽我兒子說,把子卿的鼻子打出血了呢!”——望著子卿又問:“子卿,是把你鼻子打出血了嗎?”
子卿低聲嘟噥了一個字:“是……”
母親就使勁兒擰我臉:“你把人家鼻子打出血了,又害人家挨了一頓揍,你還覺得委屈!你倒是有什麼值得委屈的?快給子卿說句賠罪的話兒!”
我嘟噥:“子卿,我再也不跟你打架了……”
子卿母親趕緊把我扯到她身後,護著我,對我母親說:“拉倒吧拉倒吧,誰跟誰呀!倆孩子打架,一個不怨一個的事兒,賠的什麼罪啊!親哥倆還有打架的時候呢!……”
子卿父親也說:“拉倒吧。”
他仍專心致志地補鞋,仍沒抬頭。
隨後我母親就和子卿母親聊起來。無非都說些她們那個松花江邊兒上的小小漁村,景緻多麼的美好,人際多麼的友善。夏季里大人孩子洗衣服洗澡是多麼的方便。聽她們那口氣,彷彿遷到城裡來住,搖身一變成為了城里人,其實是件很吃虧的事。
子卿父親這時抬起頭來了,表情很鄭重地問母親們:“後悔了?”
兩位母親互相看看,子卿母親便不作聲了,而我母親卻說:“有點兒!”
子卿父親說:“那你讓曉聲替你給我老弟寫封信,跟他商議商議,乾脆咱們兩家再遷回你們那個巴掌大的小漁村去算了!”
兩位母親又互相看了一眼。
我和子卿也不禁地互相看了一眼。我們都不留戀“臟街”。儘管我們都是在“臟街”出生的。我們都經常聽母親們在一起講她們那個小小漁村里的人和事。既然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地方,我們當然都希望父母們能下一個果斷的決心,告別城市。更準確地說,是告別這條不值得人留戀的“臟街”,帶領我們回到它那裡去。哪怕是回到父親們的山東老家去,也是我們非常之心甘情願的啊!據我們想來,中國的任何一處地方,與“臟街”比起來,肯定的都不失為一個值得祖祖輩輩生活下去的好地方吧?
兩位母親的目光,又緩緩地移在我和子卿身上。
子卿母親說:“那,兩個孩子怎麼辦?我們那兒又沒學校,他們不上學了嗎?”
我母親嘆了口氣,也說:“是啊是啊,一想到兩個孩子,這決心就不好下了呢!”
子卿父親說:“那你們以後,就不要再當著孩子們的面,說些你們那個巴掌大的小漁村多麼多麼好的話!說些你們後悔不後悔的話!我和曉聲他爹,小小的年紀就一塊兒'闖關東',先是在城邊上賴著混,後來終於和老婆孩子混進了城裡,是那麼容易的嗎?這其中的苦辣酸鹹,別人們不清楚,你們心裡還不清楚嗎?”
我母親搶白道:“咱們這兒也算城裡呀?”
子卿父親瞪起了眼睛:“怎麼不算?咱們兩家有戶口本兒沒有?有糧本兒沒有?都有!都有就是城里人!連政府也承認的城里人!你們當我們拖拽著你們往城裡混是為啥?為我們自己?不是!是為他們!……”
他用握在手裡的錐子指指子卿,指指我,接著又說:“為他們將來有文化,出息成兩個文明人,跟我們當父親的不一樣!我腿殘了,就不說我了。那就說俺那老弟!他現如今是工人階級了不是?是啦!可沒有文化的工人又是什麼?舊社會叫臭苦力,插上條尾巴人家就把你當成頭驢!拼上我們這一輩子,有苦往肚子裡咽,也得叫子卿和曉聲,跟我們不一樣!……”
子卿父親漲紅了臉,說得格外激動。
兩位母親聽著他的話,表情漸漸地肅然起來。
我和子卿也不禁地都裝出肅然的樣子。我望著子卿,覺得父輩們,是把什麼無形的,但是卻異常沉重的東西,壓在我們的身上了。子卿的眼睛告訴我,他當時心裡也是這麼覺得的。那一時刻,我們內心裡部充滿了對我們的父輩們,母親們,和我們自己的大的體恤。我們都明白了一點,無論我們多麼地討厭這一條城市邊兒上的“臟街”,看來我們也得和它常相廝守了……
“外邊有人等著沒有?”
某天,子卿在公共廁所里大聲地這麼問。
我聽出是他,不願馬上回答。
隔片刻,子卿又大聲問:“外邊就沒人等著嗎?”
我忍住笑說:“有人等著,你快點兒!”
分明的,子卿也聽出了是我的聲音,又隔片刻,在裡邊搭訕著說:“是你小子呀!”
我說:“不錯,是我。”
子卿說:“求個事兒行不行?”
我很乾脆地說:“不行!”——心想,你在裡邊屙屎,能求我什麼好事兒?難道叫我幫你使勁兒不成?
子卿低聲下氣兒地說:“行吧!我忘帶手紙了,分我一半手紙咋樣?”
我一聽,心裡別提有多幸災樂禍,說:“活該!”
他說:“'俺弟',別跟哥這樣嘛!”
只有他父親跟我父親說話,才可能這麼說。
我心想——“俺弟”是你叫的嗎?跟我來這一套?來這一套也不給你面子。
我仍因前幾天我們打那一架多少有點兒記他仇。
他說:“你就這麼不重情分啊?你忘了我對你好的時候啦?”
我說:“忘啦!”
他說:“那,我出不去,你可也別想進來。”
我說:“那你就一輩子蹲在廁所裡吧,我回家去了!”
我說完,繞著廁所跑了一圈……
子卿在廁所里高叫:“哎,哎,'俺弟'!'俺弟'你別走嘛!”
我聽了,心裡又多了幾分幸災樂禍。
但是,比較而言,在忍耐力方面難以持久的,畢竟不是子卿,是我。
子卿猜測到了我其實並沒離開,反而在廁所里大聲唱起歌來……
他也唱出了幾分幸災樂禍。
我開始覺得痛苦了。
我又憋了一會兒,實在憋不住了,終於不得不問:“你到底出來不出來哇?”
子卿說:“暫時又不想出去了!”
我說:“'俺哥',快點兒出來吧,我都要屙褲襠裡了!”
他說:“活該!你屙褲襠裡我才高興!”
接下來自然輪到我央求他了。而結果是——我走入廁所,將我帶的手紙一分為二,將面積明顯大些的那一部分,恭恭敬敬地奉獻給他……
我從廁所出來時,見他站在廁所外,沒走。
他說:“出來了?”
我說:“我又不想屙完了還蹲在裡邊唱歌!”
他得意地一笑:“我在等你。”
我說:“我可沒求你等我。”
他說:“那就算我自己樂意等。'俺弟',咱倆以後別慪氣了,啊?”
他說完,將胳膊親暱地搭在我肩上……
從此我們再也沒互相同過彆扭。我們就像當年“臟街”上互相最親愛的一對親兄弟……
在我們全班,乃至我們全校,子卿始終是學習最好的幾個同學之一。
我清楚地記得這樣一件事——小學三年級的期中考試,他又得了“雙百”。全班僅他一個學生得“雙百”。公佈成績時,老師照例對他大加誇獎。同時叫起了三個不及格的學生,教訓得他們一個個低垂下了頭。三個不及格的學生中,有一個還是留級生。
放學後,我和子卿剛走到一條胡同口,被那三個不及格的同學攔住了。分明的,他們是預謀好了,專在那兒堵截我們的。
為首的留級生氣勢洶洶地對子卿說:“翟子卿,我們早就警告過你,不許你再考'雙百',你為什麼還故意考'雙百'?”
子卿說:“那我也不能故意往不及格考吧?”
對方一聽更來氣了,當胸搗了他一拳:“你讓我們三個當眾害羞,今天我們三個也非得羞羞你不可!”
我說:“你們幹嗎欺負人!”
他一推,將我推倒在地,恐嚇道:“你又沒考'雙百',沒你什麼事兒,別找不自在!”
我爬起來,對子卿說:“子卿你別伯他們!要打就打,我幫你!”
子卿卻說:“那,你們想怎麼羞我?”
他們說——得子卿從他們胯下鑽過去才肯放過我們……
子卿聽了,默默將書包從身上取下,遞給我。
他們以為子卿真想和他們打架,都防範地擺好了姿勢。
我知道子卿是不敢和他們打架的。倒不見得是因為他多麼的怕他們。其實他是很能打架的。他內心裡根本不至於怕他們。他是怕他的父親。他實在是太怕他的父親了。他父親對於他來說,簡直就是一位上帝似的。他因和我打那一架挨了他父親的揍以後,再受到挑釁甚至受人欺負,就學會了一個忍字……
子卿又默默脫下打了好幾處補丁的褲子遞給我……
這使他們非常困惑,面面相覷,搞不明白子卿究竟是要幹什麼? ……
子卿卻說:“我鑽……”
子卿說完,子卿就雙膝跪下去了……
而他們,這時都蠻橫地笑了。他們一個個叉開兩腿,一個站在另一個的身後……
當子卿從他們第一個人的胯下鑽過之後,我發現他們第二個人將手伸進褲襠裡去了,我立刻明白了他想幹什麼……
我大叫起來:“子卿,別鑽了,他要往你身上撒尿!……”
可是尿已經撒到子卿身上了……
某些時候,某種情況之下,欺辱別人的心理快感表現在缺乏良好品德教育的孩子們身上,也是和大人們的罪過行為一樣邪惡的……
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我將我自己的書包和子卿的書包,褲子往地上一拋,像一條掐斷了鍊子的狼狗似的朝他們撲過去……
子卿見我已然和他們扭打作一團了,才開始和我一起勇猛無比地討回他失去的公道……
三個同學自感無理,也意識到他們自己欺人太甚了,先自心虛,哪裡還敢真和我們打下去?都吃了些虧,哀哀疼叫著,互相照應著擺脫了我們的無畏還擊,倉皇而逃……
子卿的褲子卻在扭打中被踩破了……
子卿不敢直接回家,跟我到了我家裡。
母親聽我講述了一遍經過,撫摩著子卿的頭說:“孩子,你也忒老實了!他們叫你從他們褲襠下鑽過去,你就真鑽啊?還脫了自己的褲子鑽!……”
子卿噙著淚說:“娘昨天夜裡剛給我補好的褲子。娘說布已經'絛'了,再也掛不住補丁了。娘囑咐我要小心在意地穿,說穿兩個月後才能給我做條新的……”
子卿說完,就哇地哭出了聲……
我這才明白,子卿他不和他們打架,子卿他脫下自己的褲子鑽他們的胯,不僅因為他怕他的父親,還因為他那條補了好幾處補丁的褲子在兩個月內是萬萬破不得的……
子卿哭得我也難過起來,哭得母親也落下了淚。母親爬上炕,翻箱倒櫃,找出一條父親的肥大的舊勞動布褲子,剪去一尺多褲腿兒,粗針大線地給子卿改成了一條他勉強可以穿的褲子。子卿穿上了它模樣顯得滑稽可笑,如同一隻從母袋鼠腹袋之中探出上半身驚詫地張望世界的小袋鼠……
我和子卿上小學四年級那一年,子卿的父親去世了。他父親是由於患胃癌去世的。當年“癌”還是一個不太常聽人提到的字。對於窮困人家來說,更是“不治之症”。甚至是糊塗之症。子卿父親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有時疼得在炕上滾來滾去。還大口大口地噴吐鮮血。那時子卿母親便驚恐地替子卿父親輕拍後心,或者撫他的胸口。那些做法當然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也絲毫減輕不了子卿父親的痛苦。而小小的子卿,則雙手端著臉盆,渾身抖抖瑟瑟地佇立炕沿前,接著父親口中噴吐出的鮮血。那對他是一件必須那樣做而又極其害怕的事。他可憐自己的父親也可憐自己的母親。父親口中噴吐出的鮮血往往濺在他身上、手上和臉上。有一天我到他家去正好碰上了那樣的情形。目睹子卿雙手哆哆嗦嗦端著的半盆鮮血我幾乎暈倒在他家裡。我雖然並沒暈倒在他家裡,卻親眼見子卿因心理過分緊張而暈倒了。半盆鮮血潑在他身上……
非但子卿,連子卿母親和我母親,當年也不知他父親得的究竟是什麼病。他母親和我母親,在那條街上逢人便問——什麼是癌?怎麼得了癌,醫生便說沒法治了?只能等死了?有沒有什麼偏方可治?當年那條街上沒有一個人能向他母親或我母親講清楚什麼是“癌”。更沒有一個人向兩位母親介紹過某種治癌的偏方。窮困的老百姓對窮困的老百姓的同情,往往也只能是相與說幾句勸慰的話,陪著唉聲嘆氣,陪著掉幾滴眼淚而已。子卿父親死前已瘦得皮包骨。臨死前他還以為,他是被肚子裡的蛔蟲害的……
是我母親幫他母親給他父親穿上壽衣的……
是我母親幫他母親將他父親發送了的……
冬天,我父親從大西北建築工地回來探家時,親自去子卿父親墳前磕過頭……
當時我父親眼中流淚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流淚。
父親對著墳頭說:“俺哥,你就放心吧!嫂子和孩子往後的日子,有你弟妹照應著呢。我看子卿這孩子很懂事,學習又好,將來一定會有出息,一定會對得起你的養育之恩……”
子卿父親活著的時候,在我們那條街上,他家的生活已是最窮的了。他父親一死,他家的日子更難過了。最初靠街道的救濟勉強度日。後來街道不救濟了。不得不靠變賣家當了。當年的窮老百姓人家,哪裡談得上有什麼“家當”可賣!所賣其實都是過窮日子離不了的東西,賣了也不值幾個錢。不賣則連買糧的錢都沒有……
不久我母親當上了街道居民組組長。那時街道上成立了一個把石棉加工成石棉線的小工廠。為了照顧生活困難的居民,允許一部分街道婦女將石棉領回家去紡。這一部分不多,而希望掙那點兒錢的人卻很多。我母親利用居民組組長的小小權力,替子卿母親爭取到了優先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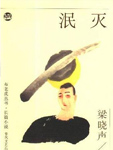
泯滅
梁晓声
當代小說
類別- 1970-01-01發表
-
232145
完全的
© www.hixbook.com
按“左鍵←”返回上一章節; 按“右鍵→”進入下一章節; 按“空格鍵”向下滾動。
